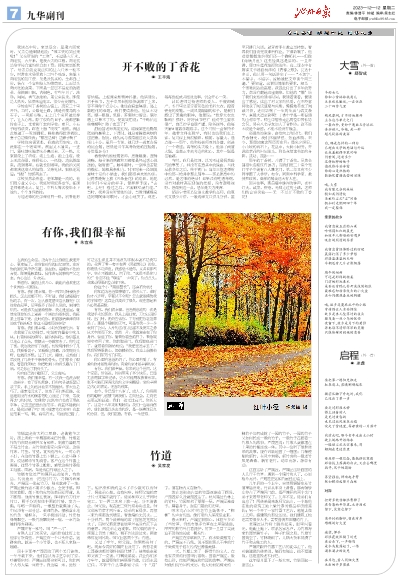发布日期:
2023年12月12日
开不败的丁香花
我读高中时,家里很穷。星期六回家时,父亲总是幽默地说:“领工资的又回来啦!”父亲所谓的“工资”,不过是六斤米,两毛钱。六斤米,是我六天的口粮,两毛钱是给学校食堂的伙食加工费。即使家里断炊了,母亲总能变戏法似的让六斤米一粒不少,时常在米袋里放上三四个鸡蛋,来抵上两毛钱的加工费。菜是没钱买的,全都自己带,装在一个容积较大的菜筒里,上面是头两天吃的蔬菜,下面是一层层不易变质的腌菜。菜筒碗口粗,古铜色,有些年月了。洗净,闻闻,香气浓浓的,用它来装菜,即使是大热天,依然味道纯正,很少有变馊的。
学校在叫丁香树的古镇上,离家三十里开外。当时,公路是土路,满是长棱角的小石子,一双新布鞋,走上几个来回就烂掉了,让人心疼。除了很冷的日子,我都把鞋拎在手上,光着脚丫走到学校。夏日,小石子晒得滚烫,踩在上面“吱吱”地响。我因此练就了一双铁脚板,鞋袜换得比谁都快,妻子总是嗔怪我:“哪里是脚?是蹄子啊!”
学校住房很紧张,我班的男生吃、住、洗都在一个寝室里,潮湿又不通风,一进门,霉味馊味腌菜味扑鼻而来。天一热,大家都染上了疥疮。疮上生泡,泡上生疮,晚上无法合眼,痒得钻心,一抓挠,流出脓血来,流到哪里,疮就长到哪里,我的指叉间都塞满这磨人的怪物。父亲见状,狠狠地骂道:“猪!”便抓药去了。
学校虽然条件差,老师却是一流的,他们既专业又专心。我班师资配备豪华,任课老师都是北大、复旦、中科大等名校毕业下放的,个个身怀绝技。
方旭老师的化学课别具一格。别看他形容枯槁,上起课来却精神抖擞。他语速快,右手板书,左手中黑板擦很快就跟了上来,容不得你半点分心。他住在寝室隔壁,遇上数理化的难题,我们便请教他,他从不动笔,瞟一眼题,思路、答案顺口溜出。偶尔遇上口算不了的,便皱皱眉说:“干吗钻这些难题啊?路子走歪了!”
舒治国老师高度近视,眼镜架在他黝黑肥硕的鼻梁上,下课时,他总爱捧着黄烟筒过把瘾。据说,他的高考成绩超过北大录取线几十分。最后一节课,他只讲一道复合场的综合题,居然是当年高考物理的压轴题,分值是20分!
教数学的杨桂霞老师,思维敏捷,逻辑清晰,每节课的例题和习题都是经过悉心挑选的,辐射面广,解难题时,一副举重若轻的模样。她极具亲和力,时不时来一段调侃意味十足的小插曲,我们都很喜欢她的课。记得那晚街上放《五朵金花》的电影,她见同学们不安分的样子,便挥挥手说:“去吧,去吧!看过之后,不要瞎唱就行啦。”当时,我并没有听懂她的话,当看到蝴蝶泉边阿哥阿妹对歌时,才会心地笑了。现在,每每想起或者提及这事,仍会开心一笑。
吕兵老师是杨老师的爱人,干瘦却威严,冬日里总爱穿着灰色的毛料大衣,蹬着锃亮的皮鞋,一副风度翩翩的样子,见我们露出了羡慕的眼神,他便说:“想穿大衣皮鞋吗?那好,好好读书吧!”他对学生要求很严,自己治学也很严谨,除备课外,他每天解8道数学题练手,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多年。他带文科班数学,有时也给我们班上课,复习课上得很精彩,精要,容量大,选点准……那年,他和杨老师双剑合璧,创造了一个奇迹:高考的头天晚上,他讲了两道大题,全都正中高考卷的靶心,其中一题是压轴题。
当时,我只是惊讶,以为不过是偶然碰巧的事罢了,并没有在意其中的缘由。当我从教多年之后,终于明白:当年三位老师射中的那三枪并非那么简单——那是偶然中的必然,是名师的绝活!如果没有吃透考纲,没有对教材高屋建瓴的把握,没有巅峰视野,想做到这一点,恐怕是天方夜谭。
胡必宁老师是位语文教学的高师,他现代文很少开讲,一般的课文只讲几分钟,甚至只讲几句话,就背着手在教室里转悠,看着我们自读完成课后作业。下课铃响了,他恭恭敬敬地给我们还一个鞠躬礼……但像《荷塘月色》这类经典还是讲的,一旦开讲,便口吐莲花地把你迷住。高二课本中有篇课文节选自杨沫的《青春之歌》,长达十多页,他只用一句话讲完了——“不加字、不漏字、不错字、流畅地把文章读个两三遍。”要知道,这看似简单的要求,却是一个很难到达的高度,我因此付出了多年的努力,都没有翻越这座高峰。但他的“懒”给了我们充裕的读书时间,我读着读着,便读出了感觉,读出了对文字的热爱,在不经意间收获了阅读速度与兴趣,慢慢地养成了阅读习惯,进而影响了一生的生活与语文教学,真是大道至简啊!丁香中学是一所普通的山村中学,师生中居然走出两位中国作协会员,另有八名学友加入了省作协。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不能不说没有缘由。
那是热浪滚滚、奋发向上的时代。我们青春勃发,我们怀揣梦想、热血沸腾。至今,那晨读晚读图历历在目:晨光夕照里,小山坡的岩石上,花丛中,大树小树旁,开满油菜花的田间地头,到处点缀读书郎的身影,或站、或卧……
那年的丁香树,开满了丁香花。虽然全国招生名额仅有28万,而我们班二十来个寒门学子中就有八人跳龙门,第二年又有不少同学圆了大学梦。如今,同窗中科学家、教授和政界、商界的精英还大有人在。
回首往事,那晨曦中雄浑的钟声,夜半灯火,咸菜,疥疮,光脚走过的土路,老师们的音容笑貌……无一不是开不败的丁香花!
学校在叫丁香树的古镇上,离家三十里开外。当时,公路是土路,满是长棱角的小石子,一双新布鞋,走上几个来回就烂掉了,让人心疼。除了很冷的日子,我都把鞋拎在手上,光着脚丫走到学校。夏日,小石子晒得滚烫,踩在上面“吱吱”地响。我因此练就了一双铁脚板,鞋袜换得比谁都快,妻子总是嗔怪我:“哪里是脚?是蹄子啊!”
学校住房很紧张,我班的男生吃、住、洗都在一个寝室里,潮湿又不通风,一进门,霉味馊味腌菜味扑鼻而来。天一热,大家都染上了疥疮。疮上生泡,泡上生疮,晚上无法合眼,痒得钻心,一抓挠,流出脓血来,流到哪里,疮就长到哪里,我的指叉间都塞满这磨人的怪物。父亲见状,狠狠地骂道:“猪!”便抓药去了。
学校虽然条件差,老师却是一流的,他们既专业又专心。我班师资配备豪华,任课老师都是北大、复旦、中科大等名校毕业下放的,个个身怀绝技。
方旭老师的化学课别具一格。别看他形容枯槁,上起课来却精神抖擞。他语速快,右手板书,左手中黑板擦很快就跟了上来,容不得你半点分心。他住在寝室隔壁,遇上数理化的难题,我们便请教他,他从不动笔,瞟一眼题,思路、答案顺口溜出。偶尔遇上口算不了的,便皱皱眉说:“干吗钻这些难题啊?路子走歪了!”
舒治国老师高度近视,眼镜架在他黝黑肥硕的鼻梁上,下课时,他总爱捧着黄烟筒过把瘾。据说,他的高考成绩超过北大录取线几十分。最后一节课,他只讲一道复合场的综合题,居然是当年高考物理的压轴题,分值是20分!
教数学的杨桂霞老师,思维敏捷,逻辑清晰,每节课的例题和习题都是经过悉心挑选的,辐射面广,解难题时,一副举重若轻的模样。她极具亲和力,时不时来一段调侃意味十足的小插曲,我们都很喜欢她的课。记得那晚街上放《五朵金花》的电影,她见同学们不安分的样子,便挥挥手说:“去吧,去吧!看过之后,不要瞎唱就行啦。”当时,我并没有听懂她的话,当看到蝴蝶泉边阿哥阿妹对歌时,才会心地笑了。现在,每每想起或者提及这事,仍会开心一笑。
吕兵老师是杨老师的爱人,干瘦却威严,冬日里总爱穿着灰色的毛料大衣,蹬着锃亮的皮鞋,一副风度翩翩的样子,见我们露出了羡慕的眼神,他便说:“想穿大衣皮鞋吗?那好,好好读书吧!”他对学生要求很严,自己治学也很严谨,除备课外,他每天解8道数学题练手,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多年。他带文科班数学,有时也给我们班上课,复习课上得很精彩,精要,容量大,选点准……那年,他和杨老师双剑合璧,创造了一个奇迹:高考的头天晚上,他讲了两道大题,全都正中高考卷的靶心,其中一题是压轴题。
当时,我只是惊讶,以为不过是偶然碰巧的事罢了,并没有在意其中的缘由。当我从教多年之后,终于明白:当年三位老师射中的那三枪并非那么简单——那是偶然中的必然,是名师的绝活!如果没有吃透考纲,没有对教材高屋建瓴的把握,没有巅峰视野,想做到这一点,恐怕是天方夜谭。
胡必宁老师是位语文教学的高师,他现代文很少开讲,一般的课文只讲几分钟,甚至只讲几句话,就背着手在教室里转悠,看着我们自读完成课后作业。下课铃响了,他恭恭敬敬地给我们还一个鞠躬礼……但像《荷塘月色》这类经典还是讲的,一旦开讲,便口吐莲花地把你迷住。高二课本中有篇课文节选自杨沫的《青春之歌》,长达十多页,他只用一句话讲完了——“不加字、不漏字、不错字、流畅地把文章读个两三遍。”要知道,这看似简单的要求,却是一个很难到达的高度,我因此付出了多年的努力,都没有翻越这座高峰。但他的“懒”给了我们充裕的读书时间,我读着读着,便读出了感觉,读出了对文字的热爱,在不经意间收获了阅读速度与兴趣,慢慢地养成了阅读习惯,进而影响了一生的生活与语文教学,真是大道至简啊!丁香中学是一所普通的山村中学,师生中居然走出两位中国作协会员,另有八名学友加入了省作协。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不能不说没有缘由。
那是热浪滚滚、奋发向上的时代。我们青春勃发,我们怀揣梦想、热血沸腾。至今,那晨读晚读图历历在目:晨光夕照里,小山坡的岩石上,花丛中,大树小树旁,开满油菜花的田间地头,到处点缀读书郎的身影,或站、或卧……
那年的丁香树,开满了丁香花。虽然全国招生名额仅有28万,而我们班二十来个寒门学子中就有八人跳龙门,第二年又有不少同学圆了大学梦。如今,同窗中科学家、教授和政界、商界的精英还大有人在。
回首往事,那晨曦中雄浑的钟声,夜半灯火,咸菜,疥疮,光脚走过的土路,老师们的音容笑貌……无一不是开不败的丁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