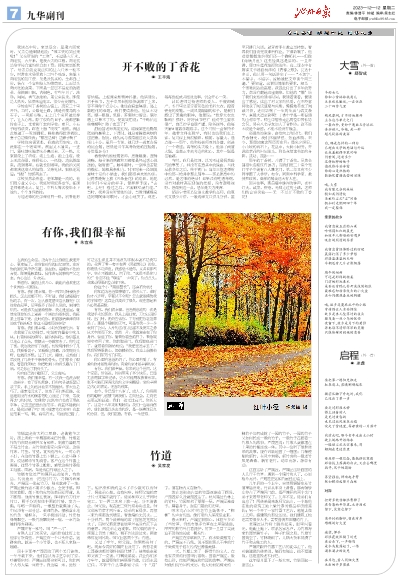发布日期:
2023年12月12日
竹道
竹墩离老街大约三里路。老街繁华之时,街上卖的一半篾器都来自竹墩。竹墩老竹的竹皮既有硬性又有韧性,制成竹器耐用不易生竹虫。卖竹货的店家向客户说,这些竹床、竹垫、竹凳,夏天能泻火,一时心情不好,在这些竹器上坐下躺上,心立马静下来,说话都带竹的清香。客户在这个竹器上摸摸,往那个竹器上瞧瞧,感觉这些竹器做工细腻、圆润,知是出自竹墩匠人之手。
竹墩有位姓严的篾匠远近闻名,有绝活。传说他有一把祖传竹刀,刀锋闪着寒光,严篾匠一抡起竹刀,阳光就碎了一地。严篾匠做竹活不用多少眼力,全凭手感,即使闭着眼,削下的竹皮每张都同样厚薄,从不断篾。他破竹像在表演,锋利的竹刀打开竹口,两手分别捏住半圆的竹端,发力一撕,咔嚓一声脆响,一根整竹就撕通了头,中间没有一丝分岔。整理竹条,把散落在地的竹条一端捏齐,一只手极速抖动,竹皮如绿绸飘空,一股竹浪飘向另一端,一束竹条被抖得齐刷刷。
严篾匠有一雅号,叫“严一刀”。
有熟人上门来买货,出的价也比街上在他家订货高些,严篾匠有一个口头许诺,远路来的,就送一个小竹器,也不枉人家跑一趟路。
四十岁那年严篾匠收了两个关门徒弟,一年半载下来,他们自认为手艺学到了家,吵着要出师。严篾匠说要出师可以,你们两个人每人编一床席子,我也编一床,比较一下,编出来和我的差不了多少就可以出师了。俩徒弟心想,这有何难,按师父编的席子尺寸来编不就行了。徒弟和师父几乎同时完工,乍一看三床席子放一起,分不清彼此。师父说,现在把三床竹席称称重量,师父那床竹席才两斤重,徒弟的重得多。再把三床竹席都放到塘里,看谁编的先沉水。二十分钟后,两个徒弟编的席子摇摇晃晃都沉水了,而师父那床漂在塘里丝毫没有沉下去的意思,两徒弟走近观察,师父编的席子,席面上仍然干燥的,看不到水渗过来。两徒弟惊诧问其故,师父回答两个字:竹道。
又过了半年,师父说,你俩都出师了吧,现如今再好的篾匠也没用了,我看老街上篾器店都用塑料制品代替了。徒弟临走前师父做了一桌饭,叮嘱徒弟说,我让你们多待半年,就是要你们再悟悟竹道,以后永远记住,不管干什么事都要守住一个“道”字,道在物内又在物外。
放在老街商店里的竹器逐渐成了摆设,严篾匠好久没做篾匠活了。秋风筛过竹林上的竹叶,竹园里积了厚厚一层。严篾匠袖着手,蹲着身子,泡在门前的阳光里。
啄木鸟在园中的老竹上敲梆子,“梆梆”的声音传出,像打更的人深夜里走来。
春天来时,严篾匠狠狠心,比往年多采了些竹笋。仍然有很多竹笋在土里躲猫猫,厚厚的枯竹叶打着掩护,竹笋一旦冒了尖就迫不及待地长成一棵秀竹。
严篾匠在家赋闲久了,有求做黄鳝笼子的,严篾匠不肯做,说不愿把那么干净的竹子做成笼子泅在污沟里诱骗黄鳝。
一天,竹墩上来了一群赏竹的文人,在他家茂密的竹园里打着转,围着严篾匠,像挖山珍,挖掘严篾匠和竹园的故事。严篾匠对他们说竹园的来历,他太奶奶陪嫁来的一棵竹子如何成就了一园的竹子,一园的竹子又如何长成一墩的竹子,一墩竹子连接着一竹墩人的故事。严篾匠说:竹墩人就像埋在土里的竹根连成一体。其中一位听了他和徒弟的故事,饶有兴致地画了一幅画:几棵瘦削的新竹,在风中舞姿,新竹旁的一截老竹凤尾森森。新竹老竹,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这画送给了严篾匠,严篾匠送给画画的人几斤干竹笋。遇到一个懂竹的人了,心里格外高兴,严篾匠把这幅竹画挂在墙上。
几年后的一个上午,突然两辆轿车从竹道里钻出来,竹影从车身上滑落,那两辆轿车停在了严篾匠门前。是严篾匠的两个关门弟子来看望老师父了。几年不见,徒弟们有出息了!两徒弟是来邀师父出山,一个邀他在他的建筑工地上做竹器为商品样房搞装饰;另一个开了一家竹器工艺店,邀他去做工艺师。搞建筑的那位还说,他们建筑工地还需要很多人手,需要搭挑和围栅的竹子。
老篾匠从竹椅上跳将起来,眼里闪着光,他跑上跑下,联系各家各户,为竹墩每家竹园销售竹子。一阵子忙碌之后,竹墩竹园掏空了,竹林疏朗了,几辆大货车装满了竹子和去做工的人。
严篾匠跟开竹器工艺店的徒弟走了,他对搞建筑的徒弟说,隔行如隔山,他不懂建筑,还是重操老本行吧。
这年腊月里下了一场大雪,竹墩顶起一座雪山。
竹墩有位姓严的篾匠远近闻名,有绝活。传说他有一把祖传竹刀,刀锋闪着寒光,严篾匠一抡起竹刀,阳光就碎了一地。严篾匠做竹活不用多少眼力,全凭手感,即使闭着眼,削下的竹皮每张都同样厚薄,从不断篾。他破竹像在表演,锋利的竹刀打开竹口,两手分别捏住半圆的竹端,发力一撕,咔嚓一声脆响,一根整竹就撕通了头,中间没有一丝分岔。整理竹条,把散落在地的竹条一端捏齐,一只手极速抖动,竹皮如绿绸飘空,一股竹浪飘向另一端,一束竹条被抖得齐刷刷。
严篾匠有一雅号,叫“严一刀”。
有熟人上门来买货,出的价也比街上在他家订货高些,严篾匠有一个口头许诺,远路来的,就送一个小竹器,也不枉人家跑一趟路。
四十岁那年严篾匠收了两个关门徒弟,一年半载下来,他们自认为手艺学到了家,吵着要出师。严篾匠说要出师可以,你们两个人每人编一床席子,我也编一床,比较一下,编出来和我的差不了多少就可以出师了。俩徒弟心想,这有何难,按师父编的席子尺寸来编不就行了。徒弟和师父几乎同时完工,乍一看三床席子放一起,分不清彼此。师父说,现在把三床竹席称称重量,师父那床竹席才两斤重,徒弟的重得多。再把三床竹席都放到塘里,看谁编的先沉水。二十分钟后,两个徒弟编的席子摇摇晃晃都沉水了,而师父那床漂在塘里丝毫没有沉下去的意思,两徒弟走近观察,师父编的席子,席面上仍然干燥的,看不到水渗过来。两徒弟惊诧问其故,师父回答两个字:竹道。
又过了半年,师父说,你俩都出师了吧,现如今再好的篾匠也没用了,我看老街上篾器店都用塑料制品代替了。徒弟临走前师父做了一桌饭,叮嘱徒弟说,我让你们多待半年,就是要你们再悟悟竹道,以后永远记住,不管干什么事都要守住一个“道”字,道在物内又在物外。
放在老街商店里的竹器逐渐成了摆设,严篾匠好久没做篾匠活了。秋风筛过竹林上的竹叶,竹园里积了厚厚一层。严篾匠袖着手,蹲着身子,泡在门前的阳光里。
啄木鸟在园中的老竹上敲梆子,“梆梆”的声音传出,像打更的人深夜里走来。
春天来时,严篾匠狠狠心,比往年多采了些竹笋。仍然有很多竹笋在土里躲猫猫,厚厚的枯竹叶打着掩护,竹笋一旦冒了尖就迫不及待地长成一棵秀竹。
严篾匠在家赋闲久了,有求做黄鳝笼子的,严篾匠不肯做,说不愿把那么干净的竹子做成笼子泅在污沟里诱骗黄鳝。
一天,竹墩上来了一群赏竹的文人,在他家茂密的竹园里打着转,围着严篾匠,像挖山珍,挖掘严篾匠和竹园的故事。严篾匠对他们说竹园的来历,他太奶奶陪嫁来的一棵竹子如何成就了一园的竹子,一园的竹子又如何长成一墩的竹子,一墩竹子连接着一竹墩人的故事。严篾匠说:竹墩人就像埋在土里的竹根连成一体。其中一位听了他和徒弟的故事,饶有兴致地画了一幅画:几棵瘦削的新竹,在风中舞姿,新竹旁的一截老竹凤尾森森。新竹老竹,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这画送给了严篾匠,严篾匠送给画画的人几斤干竹笋。遇到一个懂竹的人了,心里格外高兴,严篾匠把这幅竹画挂在墙上。
几年后的一个上午,突然两辆轿车从竹道里钻出来,竹影从车身上滑落,那两辆轿车停在了严篾匠门前。是严篾匠的两个关门弟子来看望老师父了。几年不见,徒弟们有出息了!两徒弟是来邀师父出山,一个邀他在他的建筑工地上做竹器为商品样房搞装饰;另一个开了一家竹器工艺店,邀他去做工艺师。搞建筑的那位还说,他们建筑工地还需要很多人手,需要搭挑和围栅的竹子。
老篾匠从竹椅上跳将起来,眼里闪着光,他跑上跑下,联系各家各户,为竹墩每家竹园销售竹子。一阵子忙碌之后,竹墩竹园掏空了,竹林疏朗了,几辆大货车装满了竹子和去做工的人。
严篾匠跟开竹器工艺店的徒弟走了,他对搞建筑的徒弟说,隔行如隔山,他不懂建筑,还是重操老本行吧。
这年腊月里下了一场大雪,竹墩顶起一座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