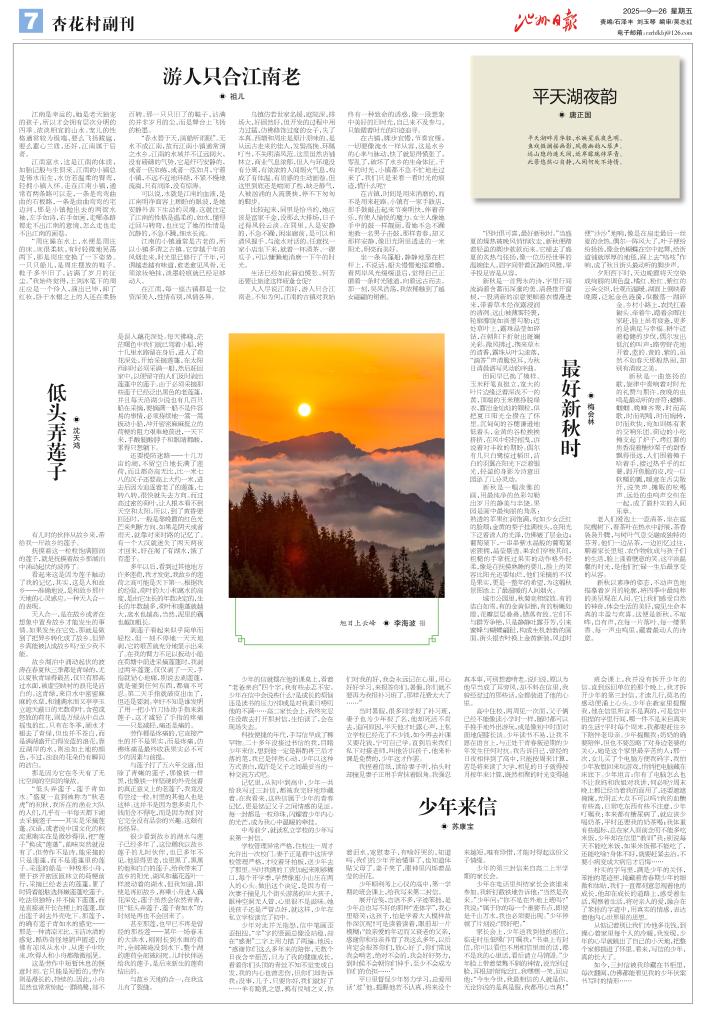发布日期:
2025年09月26日
低头弄莲子
有儿时的伙伴从故乡来,带给我一斤故乡的莲子。
抚摸着这一粒粒饱满圆润的莲子,就是抚摸着故乡那湖泊中涌动起伏的波涛了。
看起来这是因为莲子触动了我的记忆,其实,这是人和故乡——准确地说,是和故乡那片天地的心灵感应。一种天人合一的表现。
天人合一,是在故乡或者在想象中置身故乡才能发生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它处,那就是做到了把异乡转化成了故乡。但异乡真能被认成故乡吗?至少我不能。
故乡湖泊中涌动起伏的波涛在春夏秋三季都是青绿的,尤以夏秋青绿得最甚,仅只有那高过水面,被虚空映衬的浪花是洁白的。这青绿,来自水中密密麻麻的水草,和铺满水面又亭亭玉立遮天蔽日的无数荷叶。含苞或怒放的荷花,则是万绿丛中点点摇曳的红。只有在冬季,湖水才褪去了青绿,但也并不苍白,而是满湖盛开白得发蓝的浪花,靠近湖岸的水,则浊如土地的颜色,不过,浊浪的花朵仍有瞬间的洁白。
那是因为它在冬天有了无比空阔的空间的缘故。
“ 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盛夏一直到被称为“秋老虎”的初秋,我所在的渔业大队的人们,几乎有一半每天都下湖去采摘莲子——其实是采摘莲蓬。汉语,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积淀熏陶实在是微妙得很,把“莲子”换成“莲蓬”,韵味突然就没有了。但劳作不是诗,能采摘的只是莲蓬,而不是莲蓬里的莲子。采莲的船是一种梭形小舟,便于挤开密匝匝林立的荷梗前行,采摘已经老去的莲蓬。累了时倚着船舷选择嫩莲蓬吃莲子。吃法很独特:并不摘下莲蓬,而是直接剥开长在梗上的莲蓬,取出莲子剥去外壳吃下。那莲子,的确有莲子青如水的感觉— —那是一种清凉无比、玉洁冰清的感觉,酷热奇怪地销声匿迹,仿佛有凉风从水中、从莲子中吹来,吹得人和小舟都微微摇晃。
这是劳作中短暂休息的惬意时刻。它只能是短暂的,劳作则是漫长的,持续的。因此,小舟虽然也常常惊起一群鸥鹭,却不是误入藕花深处。每天拂晓,茫茫曙色中我们就已驾着小船,将十几里水路留在身后,进入了荷花深处,开始采摘莲蓬,在太阳西斜时必须采满一船,然后赶回家中,以便留守的人们及时剥出莲蓬中的莲子。由于必须采摘那些莲子已经泛出黑色的老莲蓬,并且每天沿湖少说也有几百只船在采摘,要摘满一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持续地一篙一篙扳动小船,冲开密密麻麻挺立的荷梗的阻力艰难地前进,一天下来,手酸腿酸脖子和眼睛都酸,累得只想躺下。
还要提防迷路——十几万亩的湖,不留空白地长满了莲荷,而且都奇高无比,比一米七八的汉子还要高上大约一米,进去后因为追逐着老了的莲蓬,七转八转,很快就失去方向。而过高过密的荷叶,让人根本看不到天空和太阳。所以,到了黄昏要回还时,一般是靠晚霞的红色光芒来判断方向。如果是阴天或者雨天,就靠对来时路的记忆了。有一个大汉就迷失了两天两夜才回来,好在渴了有湖水,饿了有莲子。
多年以后,看到过其他地方许多莲荷,我才发觉,我故乡的莲荷之高可能是天下第一。根据我的经验,荷叶的大小和离水的高度,是由它生长的年数决定的,生长的年数越多,荷叶和莲蓬就越大,离水也越高,当然,泥里的藕也越加粗长。
剥莲子看起来似乎简单而轻松,但一刻不停地一天天地剥,它的艰苦就充分地显示出来了。在我的臂力不足以扳动小船在荷塘中前进采摘莲蓬时,我剥过两年莲蓬。仅仅剥了一天,手指就钻心地痛,别说去剥莲蓬,就是碰到任何东西,都痛不可忍。第二天手指就破皮出血了,但还是要剥。幸好不知是谁发明了用一把小竹刀协助手指来剥莲子,这才减轻了手指的疼痛— —只是减轻,痛还是痛的。
劳作都是疼痛的,它直接产生的并不是果实,而是疼痛,仿佛疼痛是最终收获果实必不可少的因素与前提。
与莲子打了五六年交道,但除了青嫩的莲子,那像铁一样黑,也像铁一样坚硬的外壳包着的真正意义上的老莲子,我竟没有尝过一粒。村里的其他人也是这样。这并不是因为想多卖几个钱而舍不得吃,而是因为我们对它完全没有品尝的兴趣。这颇有些怪异。
很少看到故乡的湖水与莲子已经多年了,这位赠我以故乡莲子的儿时伙伴,也已多年不见。他显得更老,也更黑了。黑黑的他和白白的莲子,给我带来了故乡的阳光、湖风和藕花莲叶一样波动着的湖水,但我知道,即使是再回故乡,再乘小舟进入藕花深处,莲子虽然会依然青青,但“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的时刻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甚至那莲,也早已不再是曾经的那些莲——某年一场春末的大洪水,刚刚长到水面的荷叶,全部被淹没到水下,整个湖的莲荷全部被闷死。儿时伙伴送给我的莲子,是后来新生的莲荷结出的。
与故乡天地的合一,在我这儿有了裂缝。
抚摸着这一粒粒饱满圆润的莲子,就是抚摸着故乡那湖泊中涌动起伏的波涛了。
看起来这是因为莲子触动了我的记忆,其实,这是人和故乡——准确地说,是和故乡那片天地的心灵感应。一种天人合一的表现。
天人合一,是在故乡或者在想象中置身故乡才能发生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它处,那就是做到了把异乡转化成了故乡。但异乡真能被认成故乡吗?至少我不能。
故乡湖泊中涌动起伏的波涛在春夏秋三季都是青绿的,尤以夏秋青绿得最甚,仅只有那高过水面,被虚空映衬的浪花是洁白的。这青绿,来自水中密密麻麻的水草,和铺满水面又亭亭玉立遮天蔽日的无数荷叶。含苞或怒放的荷花,则是万绿丛中点点摇曳的红。只有在冬季,湖水才褪去了青绿,但也并不苍白,而是满湖盛开白得发蓝的浪花,靠近湖岸的水,则浊如土地的颜色,不过,浊浪的花朵仍有瞬间的洁白。
那是因为它在冬天有了无比空阔的空间的缘故。
“ 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盛夏一直到被称为“秋老虎”的初秋,我所在的渔业大队的人们,几乎有一半每天都下湖去采摘莲子——其实是采摘莲蓬。汉语,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积淀熏陶实在是微妙得很,把“莲子”换成“莲蓬”,韵味突然就没有了。但劳作不是诗,能采摘的只是莲蓬,而不是莲蓬里的莲子。采莲的船是一种梭形小舟,便于挤开密匝匝林立的荷梗前行,采摘已经老去的莲蓬。累了时倚着船舷选择嫩莲蓬吃莲子。吃法很独特:并不摘下莲蓬,而是直接剥开长在梗上的莲蓬,取出莲子剥去外壳吃下。那莲子,的确有莲子青如水的感觉— —那是一种清凉无比、玉洁冰清的感觉,酷热奇怪地销声匿迹,仿佛有凉风从水中、从莲子中吹来,吹得人和小舟都微微摇晃。
这是劳作中短暂休息的惬意时刻。它只能是短暂的,劳作则是漫长的,持续的。因此,小舟虽然也常常惊起一群鸥鹭,却不是误入藕花深处。每天拂晓,茫茫曙色中我们就已驾着小船,将十几里水路留在身后,进入了荷花深处,开始采摘莲蓬,在太阳西斜时必须采满一船,然后赶回家中,以便留守的人们及时剥出莲蓬中的莲子。由于必须采摘那些莲子已经泛出黑色的老莲蓬,并且每天沿湖少说也有几百只船在采摘,要摘满一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持续地一篙一篙扳动小船,冲开密密麻麻挺立的荷梗的阻力艰难地前进,一天下来,手酸腿酸脖子和眼睛都酸,累得只想躺下。
还要提防迷路——十几万亩的湖,不留空白地长满了莲荷,而且都奇高无比,比一米七八的汉子还要高上大约一米,进去后因为追逐着老了的莲蓬,七转八转,很快就失去方向。而过高过密的荷叶,让人根本看不到天空和太阳。所以,到了黄昏要回还时,一般是靠晚霞的红色光芒来判断方向。如果是阴天或者雨天,就靠对来时路的记忆了。有一个大汉就迷失了两天两夜才回来,好在渴了有湖水,饿了有莲子。
多年以后,看到过其他地方许多莲荷,我才发觉,我故乡的莲荷之高可能是天下第一。根据我的经验,荷叶的大小和离水的高度,是由它生长的年数决定的,生长的年数越多,荷叶和莲蓬就越大,离水也越高,当然,泥里的藕也越加粗长。
剥莲子看起来似乎简单而轻松,但一刻不停地一天天地剥,它的艰苦就充分地显示出来了。在我的臂力不足以扳动小船在荷塘中前进采摘莲蓬时,我剥过两年莲蓬。仅仅剥了一天,手指就钻心地痛,别说去剥莲蓬,就是碰到任何东西,都痛不可忍。第二天手指就破皮出血了,但还是要剥。幸好不知是谁发明了用一把小竹刀协助手指来剥莲子,这才减轻了手指的疼痛— —只是减轻,痛还是痛的。
劳作都是疼痛的,它直接产生的并不是果实,而是疼痛,仿佛疼痛是最终收获果实必不可少的因素与前提。
与莲子打了五六年交道,但除了青嫩的莲子,那像铁一样黑,也像铁一样坚硬的外壳包着的真正意义上的老莲子,我竟没有尝过一粒。村里的其他人也是这样。这并不是因为想多卖几个钱而舍不得吃,而是因为我们对它完全没有品尝的兴趣。这颇有些怪异。
很少看到故乡的湖水与莲子已经多年了,这位赠我以故乡莲子的儿时伙伴,也已多年不见。他显得更老,也更黑了。黑黑的他和白白的莲子,给我带来了故乡的阳光、湖风和藕花莲叶一样波动着的湖水,但我知道,即使是再回故乡,再乘小舟进入藕花深处,莲子虽然会依然青青,但“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的时刻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甚至那莲,也早已不再是曾经的那些莲——某年一场春末的大洪水,刚刚长到水面的荷叶,全部被淹没到水下,整个湖的莲荷全部被闷死。儿时伙伴送给我的莲子,是后来新生的莲荷结出的。
与故乡天地的合一,在我这儿有了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