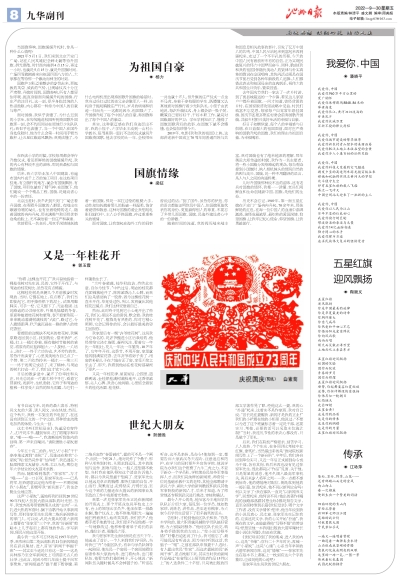发布日期:
2022年09月30日
世纪大朋友
有书自远方来,是我的最大喜乐,特别是文友的大著,读人阅文,实在快哉。然而,这个秋天,我被一本旋至的书电到了,在还没有读到正文的一个字之前,那种给血流微电加热的体验,今生头一回。
这本书叫《世纪母亲》。快递没有寄件人,打开是本书。翻到扉页,扫了眼题字和印章,“啪——啪——”,我清晰地听到体内的回响。第一声来自题词:“请阮德胜小朋友惠存”。
今年五十有二的我,早已从“小阮”干干净净地过渡到“老阮”了,是谁还在称我“小朋友”呢?显然是作者“仙风君”。我迅速在大脑里搜索文友储存,无果。本以为是,哪位老年大学结业的文友前来求教。
然而,随即看到落款:“张家军”,方才“哦——”出一口长叹。张家军先生——已是将军,但我愿意认定他为师者——不要说喊我“小朋友”,即便呼我“新兵蛋子”,我也会脆生生地应答。
这声“小朋友”,猛地将我扔回到20世纪90年代初入伍到火箭兵部队的时光里。当年,我放弃高考带着携笔从戎的“志向”一头扎进火热的军营时,搁下诗歌开始从事新闻写作,那时张家军先生是第二炮兵新闻事业的掌门人。可以说,凡是火箭兵的重大新闻上都署有“张家军”三个字,我的“好新闻”剪贴本上几乎每页上都有他的作品,学写新闻,便是从他这里开始。
最令我一生不可忘怀的是1997年的秋季,我和来自第二炮兵部队的21位新闻报道员在武汉集结,进入首届“新闻干事提干班”——其实至今还是只有这一届——这是兵种部乃至全军新闻史上可谓前无古人的壮举。出此言,是因为那几年战士提干向军事聚焦,“新闻报道员”提干摁下暂停键。第二炮兵突然“春雷破冰”,提的可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班21人,绝对是炸了个罍子。那种从形势到时机、从需求到远见,其中的谋划与运作、困难与阻力,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当时我在部队得知这个消息告诉他人时,都以为我是想提干想疯了。张家军先生以他远见卓识的胸襟、服务打赢的自信,开山而行、架梁而过,走得坚实、行得长远,至今这个班的力量还在火箭兵的新闻事业及至政治工作中发挥着光和热。
我第一次见张家军先生正是在新闻班的开班式上。那个开班式也是军校史上少有,台上的领导比学员多。他坐在第一排最东侧,整个仪式上,他不停地用眼光一遍遍地扫视着我们,始终笑笑的。我们很多人他都手把手地教导过,我们很多作品他都一字一句地修改过。他那种看着弟子成长的亲热,像位长者,更像是大哥。
我与张家军先生面对面是在当天下午,他送走了首长,一个人来到我们学员队,当时我已“升”为副区队长,有幸与学员队领导一起陪同。他先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看住宿条件和大家的内务。进门看内务,出门看队伍。他看完我们叠的被子,开心地说:“新闻队伍关键时候是不会掉链子的。”听话在听音,这不是表扬,是命令!他每到一室,都要告诉大家武汉冬天湿冷,注意适应和防护,在学习的同时要多多宣传学院。他说学院为办我们这个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亚于新办一个学员队。学院使命是培养军事指挥人才,而我们是纯粹的新闻班,师资仅一位是基础系教中文的老师,其他全部聘请于武汉大学、湖北大学的新闻教授和武汉其他军事院校的新闻人才。后来才知道,为了师资他还专程到武汉进行挑选、审核和确认。
最令人开心的是,他反客为主地向学员队队长介绍大家,每见到一位学员,他如数家珍,说姓名、讲作品,甚至还有糗事,为大家今后学员生活留下了很多搞笑的话头。
告别时,才轮到他说区队长和我。“你是本学院的,最大职责就是辅助学员队搞好管理,为大家搞好服务。”他对区队长说完,转身将手搭到我的左肩上,“你小说写得不错!”好像后边还说了什么,我可能忘了,最可能是没有听进去。因为当时听到这话,我脑子一“嗡”。之前在部队申报提干人选时,有人提出我是“作家”,而这次提拔的是“新闻干事”,差点被刷下来。其实当时我的新闻作品超过“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15件以上”的入选条件二十多倍,只是被出版的四部文学著作晃了眼。经他这么一提,我的心“扑通”起来,这着实不是作家班。我对自己说:“首长是在提醒我,新闻才是我的正业!”我们的小袄都在他的小柜里,他说过:“不要以为进了这个班就标志着一定是干部,还要实习、考核,必要的话可以采取末位淘汰制!”当时,我连礼节性的表决心都没有,只是敬个了军礼。
后来,我们在院校严格要求、刻苦学习,人人发热、个个生光,在各项评比考核中扛红旗、拿奖状,当然最出彩的是“推动院校新闻写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半年后,我们各自回到单位实习,又近一年后正式接到命令成为干部,各有其岗。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张家军先生,彼此都是以“作品”见面。关于他,只是零星的消息,他不久调入最高军事机关,再后来步入将军之列……我一点都不感到惊奇,他的德能绝对配位。倒是收到他的一部长篇,惊讶起来,他不是以新闻立命吗?何以文学了?我在部队一直是“以新闻养文学”,回想起来,他何尝不是?他出的著作《崛起的战略部落群》《苍生咏》都是报告文学,直至全面转型到长篇《世纪母亲》。哪个文字工作者,没有文学情怀?想来,他当年说到我的小说是真心、是本意。张家军先生记住我的,应该还是文学。我的心又开始“扑通”,我现在的文学,还能获得他“写得不错”的赞誉吗?很想呈他一本我刚出版的火箭军题材长篇小说《东风擘》,但还在犹豫。
《世纪母亲》到了我的案桌、进入我的内心,这是“书缘”;穿行二十多年时光,再喊一声“小朋友”,这是“心缘”;心系当年率领的火箭军新闻方阵,这是“情缘”——张家军先生在每本书上都拓上一枚刻有这六个字的篆印,应该是他的心迹吧?
张家军先生是我的世纪大朋友。
这本书叫《世纪母亲》。快递没有寄件人,打开是本书。翻到扉页,扫了眼题字和印章,“啪——啪——”,我清晰地听到体内的回响。第一声来自题词:“请阮德胜小朋友惠存”。
今年五十有二的我,早已从“小阮”干干净净地过渡到“老阮”了,是谁还在称我“小朋友”呢?显然是作者“仙风君”。我迅速在大脑里搜索文友储存,无果。本以为是,哪位老年大学结业的文友前来求教。
然而,随即看到落款:“张家军”,方才“哦——”出一口长叹。张家军先生——已是将军,但我愿意认定他为师者——不要说喊我“小朋友”,即便呼我“新兵蛋子”,我也会脆生生地应答。
这声“小朋友”,猛地将我扔回到20世纪90年代初入伍到火箭兵部队的时光里。当年,我放弃高考带着携笔从戎的“志向”一头扎进火热的军营时,搁下诗歌开始从事新闻写作,那时张家军先生是第二炮兵新闻事业的掌门人。可以说,凡是火箭兵的重大新闻上都署有“张家军”三个字,我的“好新闻”剪贴本上几乎每页上都有他的作品,学写新闻,便是从他这里开始。
最令我一生不可忘怀的是1997年的秋季,我和来自第二炮兵部队的21位新闻报道员在武汉集结,进入首届“新闻干事提干班”——其实至今还是只有这一届——这是兵种部乃至全军新闻史上可谓前无古人的壮举。出此言,是因为那几年战士提干向军事聚焦,“新闻报道员”提干摁下暂停键。第二炮兵突然“春雷破冰”,提的可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班21人,绝对是炸了个罍子。那种从形势到时机、从需求到远见,其中的谋划与运作、困难与阻力,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当时我在部队得知这个消息告诉他人时,都以为我是想提干想疯了。张家军先生以他远见卓识的胸襟、服务打赢的自信,开山而行、架梁而过,走得坚实、行得长远,至今这个班的力量还在火箭兵的新闻事业及至政治工作中发挥着光和热。
我第一次见张家军先生正是在新闻班的开班式上。那个开班式也是军校史上少有,台上的领导比学员多。他坐在第一排最东侧,整个仪式上,他不停地用眼光一遍遍地扫视着我们,始终笑笑的。我们很多人他都手把手地教导过,我们很多作品他都一字一句地修改过。他那种看着弟子成长的亲热,像位长者,更像是大哥。
我与张家军先生面对面是在当天下午,他送走了首长,一个人来到我们学员队,当时我已“升”为副区队长,有幸与学员队领导一起陪同。他先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看住宿条件和大家的内务。进门看内务,出门看队伍。他看完我们叠的被子,开心地说:“新闻队伍关键时候是不会掉链子的。”听话在听音,这不是表扬,是命令!他每到一室,都要告诉大家武汉冬天湿冷,注意适应和防护,在学习的同时要多多宣传学院。他说学院为办我们这个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亚于新办一个学员队。学院使命是培养军事指挥人才,而我们是纯粹的新闻班,师资仅一位是基础系教中文的老师,其他全部聘请于武汉大学、湖北大学的新闻教授和武汉其他军事院校的新闻人才。后来才知道,为了师资他还专程到武汉进行挑选、审核和确认。
最令人开心的是,他反客为主地向学员队队长介绍大家,每见到一位学员,他如数家珍,说姓名、讲作品,甚至还有糗事,为大家今后学员生活留下了很多搞笑的话头。
告别时,才轮到他说区队长和我。“你是本学院的,最大职责就是辅助学员队搞好管理,为大家搞好服务。”他对区队长说完,转身将手搭到我的左肩上,“你小说写得不错!”好像后边还说了什么,我可能忘了,最可能是没有听进去。因为当时听到这话,我脑子一“嗡”。之前在部队申报提干人选时,有人提出我是“作家”,而这次提拔的是“新闻干事”,差点被刷下来。其实当时我的新闻作品超过“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15件以上”的入选条件二十多倍,只是被出版的四部文学著作晃了眼。经他这么一提,我的心“扑通”起来,这着实不是作家班。我对自己说:“首长是在提醒我,新闻才是我的正业!”我们的小袄都在他的小柜里,他说过:“不要以为进了这个班就标志着一定是干部,还要实习、考核,必要的话可以采取末位淘汰制!”当时,我连礼节性的表决心都没有,只是敬个了军礼。
后来,我们在院校严格要求、刻苦学习,人人发热、个个生光,在各项评比考核中扛红旗、拿奖状,当然最出彩的是“推动院校新闻写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半年后,我们各自回到单位实习,又近一年后正式接到命令成为干部,各有其岗。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张家军先生,彼此都是以“作品”见面。关于他,只是零星的消息,他不久调入最高军事机关,再后来步入将军之列……我一点都不感到惊奇,他的德能绝对配位。倒是收到他的一部长篇,惊讶起来,他不是以新闻立命吗?何以文学了?我在部队一直是“以新闻养文学”,回想起来,他何尝不是?他出的著作《崛起的战略部落群》《苍生咏》都是报告文学,直至全面转型到长篇《世纪母亲》。哪个文字工作者,没有文学情怀?想来,他当年说到我的小说是真心、是本意。张家军先生记住我的,应该还是文学。我的心又开始“扑通”,我现在的文学,还能获得他“写得不错”的赞誉吗?很想呈他一本我刚出版的火箭军题材长篇小说《东风擘》,但还在犹豫。
《世纪母亲》到了我的案桌、进入我的内心,这是“书缘”;穿行二十多年时光,再喊一声“小朋友”,这是“心缘”;心系当年率领的火箭军新闻方阵,这是“情缘”——张家军先生在每本书上都拓上一枚刻有这六个字的篆印,应该是他的心迹吧?
张家军先生是我的世纪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