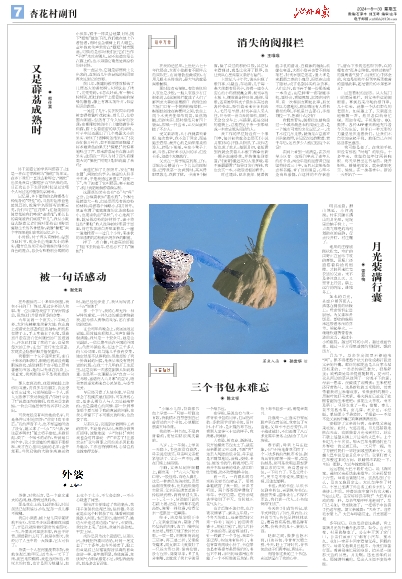发布日期:
2024年08月30日
消失的阅报栏
在我的记忆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会,大街小巷都有不同样式的阅报栏。有用细铁丝做成的,有用几根木头拼成的,最大气的就是阅报橱窗。
那时没有电视机,有收音机的人家也是少数,一般人家很少有订报纸的,因此阅报栏就成了人们了解国家大事的重要窗口。我所住的大院门口有一个简陋的阅报栏。一根细铁丝拴在两棵树之间,铁丝上两个木夹夹住报纸两角,虽然简陋,但很实用。那时报纸只有四个版面,报纸一挂出来,正反面就围拢了不少人。
受父亲影响,从小我就喜欢看报。每次放学,我不急于回家,而是跑去看报。最开心的是如果报夹前没人,便取下报纸,坐在小凳子上看。当然,有好多不认识的字,但没关系,知道个大概就行。
父亲在一所学院宣传部工作。学院办公楼前有一个长长的阅报廊,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时,高兴得眼里放光。我数了数,一共有9个橱窗,除了看过的那份日报,其它从未看到过,真是让我开了眼界,也让我从心里羡慕父亲好有福气。
上世纪八十年代,街头出现了报刊亭。马路边、车站旁,几乎每一条大街都有报刊亭,仿佛一座令人安心的小岛默默矗立着。报刊亭的木板上,摆放着各种日报、晚报、周报,还有被塑料夹子悬挂在高处的各种杂志,吸引着来来往往的路人。尤其是早晨,报刊亭前人来人往,只为买一份当天的报纸。那时,无论公交车上、马路旁,还是公园的座椅上,总能看见手拿一张报纸或一本杂志低头阅读的人。
我工作的单位附近有一个报刊亭,每月初我就会去那买《小说月报》和《诗刊》。时间久了,我和老板也成了熟人。每到月初,老板看到我就会笑着从木板下面拿出新一期杂志递给我,并热情地推荐道:“《读者》最近买的人很多哦,要不要翻翻看?”如果口袋有零钱,我也会买一本,不能驳老板的面子。
时过境迁,似水流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自媒体的崛起,纸媒在衰退,大街小巷再也看不到阅报栏,报刊亭倒是还在,但大多是卖烟酒之类的小商品,报纸杂志成了陪衬,成了名副其实的杂货亭。人们出行,也不再手握一份报纸或一本杂志,而是捧着一部智能手机,刷抖音,看短视频,沉浸在网络里。有一次和朋友聊起此事,朋友不以为意地说,现在哪还有人看书看报的啊,手机里什么都有,手指划拉一下,想看什么没有?
我惘然若失,阅报栏也曾构建过一个城市最基本的阅读生态,是一个城市可贵的文化记忆之一,这才不过几年光景,就悄无声息被岁月洪流掩埋,在记忆深处静默着。若干年后,还有多少人能记起这个名词?
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在苏州某小区有一家报刊亭成了老年人的打卡点,两位年迈的经营者已经坚持将近三十年,而且只卖报纸杂志和书籍。看了这则消息,心里不免有些感慨,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留存下来的这些报刊亭,真的颇有点“孤身走暗巷,对峙过绝望”的孤勇者气势了。而我们心中怀念的,究竟是那些年报刊亭所承载着的温暖故事,还是曾经的不知愁岁月?
回想看报的经历,从大院门口的简易报栏,到父亲单位的阅报廊,再到后来出现的报刊亭,几十年来,就像一个认识很久的老朋友,如果遇上了,天南海北地畅聊一番,然后各自转身忙碌。而如今呢,手机微信、QQ、微博、各种APP铺天盖地充斥着今天的生活,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总是压迫着我们,让我们不自觉地拿起手机,放任自己在网络世界里漫游。
我可能是老了,在我的手机里没有那些“时髦”的软件。十多年来,我坚持每年订两份晚报。每天早晨坐在书桌前,摊开报纸,静静地阅读,就会感到充实、愉悦。在一抹墨香中,新的一天开始了……
那时没有电视机,有收音机的人家也是少数,一般人家很少有订报纸的,因此阅报栏就成了人们了解国家大事的重要窗口。我所住的大院门口有一个简陋的阅报栏。一根细铁丝拴在两棵树之间,铁丝上两个木夹夹住报纸两角,虽然简陋,但很实用。那时报纸只有四个版面,报纸一挂出来,正反面就围拢了不少人。
受父亲影响,从小我就喜欢看报。每次放学,我不急于回家,而是跑去看报。最开心的是如果报夹前没人,便取下报纸,坐在小凳子上看。当然,有好多不认识的字,但没关系,知道个大概就行。
父亲在一所学院宣传部工作。学院办公楼前有一个长长的阅报廊,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时,高兴得眼里放光。我数了数,一共有9个橱窗,除了看过的那份日报,其它从未看到过,真是让我开了眼界,也让我从心里羡慕父亲好有福气。
上世纪八十年代,街头出现了报刊亭。马路边、车站旁,几乎每一条大街都有报刊亭,仿佛一座令人安心的小岛默默矗立着。报刊亭的木板上,摆放着各种日报、晚报、周报,还有被塑料夹子悬挂在高处的各种杂志,吸引着来来往往的路人。尤其是早晨,报刊亭前人来人往,只为买一份当天的报纸。那时,无论公交车上、马路旁,还是公园的座椅上,总能看见手拿一张报纸或一本杂志低头阅读的人。
我工作的单位附近有一个报刊亭,每月初我就会去那买《小说月报》和《诗刊》。时间久了,我和老板也成了熟人。每到月初,老板看到我就会笑着从木板下面拿出新一期杂志递给我,并热情地推荐道:“《读者》最近买的人很多哦,要不要翻翻看?”如果口袋有零钱,我也会买一本,不能驳老板的面子。
时过境迁,似水流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自媒体的崛起,纸媒在衰退,大街小巷再也看不到阅报栏,报刊亭倒是还在,但大多是卖烟酒之类的小商品,报纸杂志成了陪衬,成了名副其实的杂货亭。人们出行,也不再手握一份报纸或一本杂志,而是捧着一部智能手机,刷抖音,看短视频,沉浸在网络里。有一次和朋友聊起此事,朋友不以为意地说,现在哪还有人看书看报的啊,手机里什么都有,手指划拉一下,想看什么没有?
我惘然若失,阅报栏也曾构建过一个城市最基本的阅读生态,是一个城市可贵的文化记忆之一,这才不过几年光景,就悄无声息被岁月洪流掩埋,在记忆深处静默着。若干年后,还有多少人能记起这个名词?
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在苏州某小区有一家报刊亭成了老年人的打卡点,两位年迈的经营者已经坚持将近三十年,而且只卖报纸杂志和书籍。看了这则消息,心里不免有些感慨,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留存下来的这些报刊亭,真的颇有点“孤身走暗巷,对峙过绝望”的孤勇者气势了。而我们心中怀念的,究竟是那些年报刊亭所承载着的温暖故事,还是曾经的不知愁岁月?
回想看报的经历,从大院门口的简易报栏,到父亲单位的阅报廊,再到后来出现的报刊亭,几十年来,就像一个认识很久的老朋友,如果遇上了,天南海北地畅聊一番,然后各自转身忙碌。而如今呢,手机微信、QQ、微博、各种APP铺天盖地充斥着今天的生活,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总是压迫着我们,让我们不自觉地拿起手机,放任自己在网络世界里漫游。
我可能是老了,在我的手机里没有那些“时髦”的软件。十多年来,我坚持每年订两份晚报。每天早晨坐在书桌前,摊开报纸,静静地阅读,就会感到充实、愉悦。在一抹墨香中,新的一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