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2025年02月28日
他何曾有“耕余”?
出版社编辑将已故好友吴世民遗著样书寄来,委托我校对并给这本书写篇“序言”。打开快递包裹,看到书名《南山耕余录》几个字,我不禁泪眼潸然:“世民啊,你何曾有过‘耕余’?”
我与世民相交时间不算太长,只有十余年,但交着交着,渐成挚友。在我的印象里,他始终是忙忙碌碌的。世民常称自己是“耕夫”,我感觉这个自称挺“对”他的。他似乎每天都在“挖栽种浇收”,“唧唧复唧唧”,没有一刻消停过。刚开始,我十分疑惑:你一个大学老师,没有学生升学的压力,怎么会这么忙?交往久了,终于理解了:他确实忙,比我想象的还要忙。因为,有那么多“田地”需要他去“耕耘”。而且,以他喜欢较真碰硬的做事风格,花费时间和精力之多可想而知。同时,我也由衷地认为,他的“忙”,忙得确有价值,有很大价值!
一、深耕学术“田地”,钻研既深且广
世民最喜欢一个词——厚积薄发。他认为,作为一个学者首先要有深厚的“内功”,必须具备丰厚的学术积淀,要“致广大而尽精微”——一方面,要使自己具备宏观视野和广泛覆盖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掌握既“微”且“精”的知识。怎样达到这种境界?“读书,多读书!”世民曾回忆自己的学生生涯说“每上一所新的学校,图书馆里,除了英语之类的书,差不多都被我扫荡一空”。参加工作后,他读书依旧“ 贪婪成性”。与专业相关联的书,他广泛读,深入读;与专业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的书,只要发现有价值或者感兴趣,他必设法罗致,饭不吃也要把它看完。海量读书,虽然占用了他的不少生命空间,但也极大地培厚了他的学养,增强了他的学力。自然,做起学问来也就裕如了。
打开2022年出版的他的学术专著《碰撞·融合·创生——吴越楚文化交融视野下的池州历史变迁》,你就会发现,这本35万字的专著内容极其闳富,系统阐述了从商代中晚期一直到当代池州地域文明的发展演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技、地理、宗教、考古、农业、建筑、冶炼、造纸诸多领域,有许多发现和创见,比如,“宣纸本为池纸。”他认为,“称为宣纸的原因是,该纸的产地是池州地域内的秋浦县。秋浦县在唐代的前期属宣州管辖。此段时间内,泾县以及宣州其他各县均未产纸(《新唐书》《元和郡县志》记载)。乃至宋时,宣州其他各县仍不产纸(《宋史》)。故至北宋时,宣纸一词已成为池纸固定的专指。”这一发现,还原了中国造纸文明一段真实状况。还有,他对池州市和黄山市境内古“ 南江”遗址路线的发现及论证,修正了《水经注》研究权威陈桥驿教授“古南江不存在”的论断,是当代《水经注》学研究的一个新突破。
这本《南山耕余录》虽然在世民笔下仅仅是“耕余之录”,但是依旧充满着学术色彩。其中,上篇第三章到第五章,学术色彩最浓。在第三章《南山悟道录》里,他从社会原因、理论溯源、“《四书》学”内涵等方面解析了《四书》与“三教归一”的因缘关系,很有思想启发性;他辩证比对了老子的“圣人”学说和庄子的“真人”学说,指出“‘真人学说’是对‘圣人学说’的补充、深化和发展”,拓展了现代学者钱穆关于老子、庄子学说歧异的理论。在第四章《南山寻古录》,他考证了长江文化与青弋江文化的地理衔接、陵阳山与道教文化、南太原郡在池州的迁转、唐代大诗人李白流寓秋浦的文化之旅、杜牧与《清明》诗的创作、画坛巨匠黄宾虹旅居池阳的绘画创作、宋朝大书法家沈辽隐居齐山的诗歌创作等。第五章《南山谈艺录》则就诗歌创作、绘画艺术、书法技法、文体兴盛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有些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比如“书拘于形划,画拘于形色者,匠也;唯书以写心,画以达意者,可以为师”“定画品先察修养”“鹧鸪意象自李白始大”“诗有画境、情境、意境”等。
即使在偏于记录和感悟生活的上篇第一章《南山樵采录》、第二章《南山闲居录》和分类汇集个人诗词歌赋的下篇第六到第十一章,也不乏学术气息。在《南山樵采录》中,他探析了池州的茶文化、造纸技术、动植物资源等;在《南山闲居录》中,他又对传统节俗、饮食、生死文化等展开论述。他的诗词歌赋大量用典,尽显学者之风。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其《池州赋》《杏花村赋》与四十余首咏史诗。这些诗赋非有厚实的史学功底不能为。
为什么一本随笔性质的文集有如此浓郁的学术色彩?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求真知、觅真理已经成为他的生命品质。”
二、执着池州地域文化研究与保护,开辟荆榛成“良田”
池州建市时间短,地域文化研究基础薄弱,系统研究接近荒芜。世民阅历丰富,视野宽阔,涉猎广泛,原本可以选择一些“时尚”的专业作为主攻方向。这样,可以“多快好省,易出成果”。可他却不顾劝阻,毅然决然地凝心于池州地域文化研究。我曾问过世民:“你研究生读的是科技哲学史专业,为什么现在却搞起了池州地域文化研究来?这可是个冷门,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经验可借鉴,难出成果啊!”世民回答道:“但尽人事,莫问前程!”顿了会,他又说:“我搞研究,不是为了凑热闹,是看社会和地方是否有需要,是否有价值。”说着说着,他的眼里泛起光:“池州是一个既年轻又古老的城市。在这片土地上,距今约30万年就出现了华龙洞人,这有可能是东亚地区向智人演化的最早古人类。商代中晚期,这里便有了青铜文明和稻作文化。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有了建城历史。作为池州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么灿烂的地域文化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研究地域文化,首先需要有文献做底。新中国成立以来,池州历经多次撤建,文献档案流落各地,找寻异常困难。为了找到所需文献,他四处奔走。既到过北京、上海、合肥、安庆等处图书馆、档案馆,也走街串巷、进村入户翻找资料。史书、方志、家谱、文集、回忆录… …一本本地翻阅,一遍遍地“耙梳”,看过的书籍资料难以计数。世民视力不好,看书喜欢眯着眼。至今,我的眼前还时不时闪现一幅画面:月儿高挂天空,与池州城西郊某小区顶楼一个窗户透出的光遥相呼应。世民置身窗前故纸堆中,手拿一本线装书,凑着台灯,眯缝着眼分辨着… …
世民尤其注重田野调查。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格物致知”,田野调查曾经是古人治学的“刚需”:孔子周游列国而后删述“六经”,司马迁为著《史记》“行万里路”,郦道元踏遍千山万水成就《水经注》,梁思成、林徽因冒着战火辗转全国各地考察研究古建筑……但是,毋庸讳言,近年来,浮躁之风蔓延至学术研究领域。在文史界,能潜心耙梳古籍的人都不多,一些研究者甚至要靠“百度”过活,更不要说去做“费钱费力费时间”的田野调查了。有人曾委婉地提醒世民,“你这学问做得太累了,效率太低了。”世民笑了笑,依然故我。
他曾四十多次前往古石城县、秋浦县遗址所在地考察,厘清了古石城县、秋浦县文化发展脉络。为了寻找春谷古县城遗址,他冒着高温酷暑跑了一次又一次。有时,头天去看了,晚上躺在床上有了疑问,第二天立马又去现场。为了寻找古南江故道,他结合郦道元《水经注》和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的记载,跋山涉水仔细勘察,并请人用无人机航拍进行辨析,终于弄清了古南江的大致流程、流域。他的田野考察经历,这本《南山耕余录》上篇第二章《南山闲居录》、第四章《南山寻古录》和下篇诗词诸章有所记载和反映,但这仅仅只是他诸多田野考察的一小部分。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两件事就没有记录。
第一件事在2023年7月。记得一天世民告诉我,说他考察了多次,认为唐朝大诗人李白的《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一诗的创作大概率与青阳县陵阳镇境内琉璃岭有关。我很兴奋,说,“这个发现很好。我抽时间来拍一个与之有关的电视短片。”8月份,我发现他病情加重,走路都有些摇摇晃晃,就说,“你身体已经这样了,暂时不去。等你身体恢复了我们再去。”9月底的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兴奋地说:“可以基本确定了!李白的《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一诗写到琉璃岭。这诗的第一句是‘霜凋楚关木’。我刚又去了琉璃岭,了解到这里过去有个寺庙就叫‘郢关寺’。综合其他因素,可以确定我之前的推断是正确的。”我顿时无语——世民,你病情很重,你正在进行血液透析治疗啊!
第二件事发生在世民去世前的一个月。当时,我正带着团队拍摄寻古秋浦县系列电视专题。他知道了,要陪我们一起去。我以他需要定期透析治疗为由没有答应。他反复说他不是天天透析,透析间隙可以去。不去,心里憋得难受,更不利于治疗。我知道他的个性,拗不过他,只能让他前往。那一次,找到了《光绪贵池县志》记载的陶渊明衣冠冢遗址,他高兴得像个孩子。
这些年,世民究竟跑了多少路?考察了多少地方?考察什么?这些现在已经无法寻找答案了,我的脑子里只浮现出一句诗词“八千里路云和月”。
功不唐捐。这种独特的“吴氏研究法”虽然在某些“聪明人”看来“很笨”,但正是依靠这种“很笨”的研究方法和十多年如一日寂寞中的坚守,世民硬是在池州地域文化研究领域开拓出一片又一片“良田”:他初步还原了吴、越、楚文化碰撞、融合,从而创生出池州地域文明的过程与内容;他系统地梳理出池州府治及辖县县治的历史变迁,深度发掘了杏花村文化、古石城— — 秋浦文化与九华山、齐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他考证出李白现存关于池州诗歌创作的全部篇目,并系统阐释了这55首诗歌涉及的具体地点、创作背景、内容、精神内核与意象特点。这些,从《南山耕余录》中可以管窥之。
世民潜心研学、淡泊名利,直至离世,职称还只是个“副教授”。但他的学术能力却得到了业界广泛认可,被聘为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会员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特聘研究员。
我想,这些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学术成绩的充分肯定,更意味着池州地域文化研究得到了省里、国家乃至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三、乐种“公田”,精耕“自留地”
世民在世之日,我曾笑他有两个特别之“好”。
一是“好管闲事”。
记得去年九月的一天,他跑到我单位,找到我说:“ 青阳县杨田镇境内有好几座古老的石拱桥,非常漂亮。老江,你是记者,去拍拍,呼吁要加强保护。”我说我们去报道要申报。过了两天,他就打来电话“申报通过了没?要尽快报道,引起方方面面的重视。”那段时间,由于其他方面工作较多,我们没有时间去采访。他就隔三差五地打电话催促。我哭笑不得,回他说“你急什么?你哪是文管所的?好管闲事了啊!”他说:“这怎么是闲事呢?这是公众的事,人人有责。我发现了就要管。”不久,我们摄制了专题片《十里东堡悠悠古桥》。
这本《南山耕余录》还收录一份市政协提案——《关于建立昭明文化遗址公园的建议》。世民不是政协委员,这份提案怎么会出现在他的文集里呢?原来,他发现始建于唐朝的梁昭明太子庙遗址尚存,但没有得到恢复和开发,便邀请一名文艺界市政协委员实地考察,并一同撰写了这份建议,由该委员提交上去。这份提案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目前,梁昭明太子庙遗址保护已被列入相关保护规划。
有些单位举办职工文化培训,邀请世民作历史文化讲座。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去,不管有钱没钱。他说,这是机会,可以传播池州历史文化。《池州市志》编辑工作启动,他主动要求加入,说“只要让我为修志出把力,可以不要工资,不挂名”。有些同行治学不严谨,不做认真考证,“百度”上“荡”点资料拼凑成文就发表,他“视同寇仇”。李白笔下的“水车岭”遗址被破坏,他痛斥相关负责人……有关他“好管闲事”的事例不胜枚举。有人说:“你一个学者,安静做你的学问就行了。管那么宽干吗?”他回答道:“做学问的初心是什么?经世致用!如果因为要做学问,就两耳不闻窗外事。那样的学问不做也罢。”
二是“好为人师”。
世民在自己所在的池州开放大学(原池州电大),先后担任学校办公室、教学处和教研室副主任,教学、管理与科研任务相当重,加上他做事较真,又“好管闲事”,本来就够忙碌的。有几年,还去池州学院兼职教学。当时他职称不高,课时费很低。显然,兼职不是为了钱。我见他太忙了,怕他身体吃不消,就劝他:“你忙得过来吗?你当老师没当够吗?”他憨憨一笑:“当老师永远当不够。”然后解释说,这些大学生就是文化传播的火种。激活他们对文化传承的热情,那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世民在池州学院兼职教学,有两个学生对池州地域文化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一个叫万余胜,另一个叫杨明星,都来自皖北阜阳市。世民就经常给他们“开小灶”。比如,利用节假日带领他们到池州各地考察历史文化,激发他们多读书。
在世民的影响下,万余胜和杨明星大学毕业后都留在了池州,都对历史文化研究感兴趣。其中,万余胜在一家艺培机构执教,他喜欢把学生带到老师吴世民家接受文化熏染。自然,这些人又成了世民的学生。不过,把学生招到家中,世民可是要“赔本”的。万余胜曾经回忆过那段经历:“毕业后我陆续带了好几个‘徒子徒孙’到吴老师家里。每个人吴老师都热情欢迎,小课堂一开就是三四个小时。不收费。”“他靠记忆普及池州历史文化,如数家珍,精确到年月日。”一个叫陈峥的学生对一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吃饭吴老师从不让我们结账,都是他自掏腰包。一般人往往是说说而已,最多推三次就结束了这个回合。而他每次都真付钱。他说我们学生没有钱。”陈峥他们并不知道,当时,他们敬爱的吴老师其实也没什么钱。依靠住房公积金和亲戚朋友的借款,他才好不容易在房价远低于城中的城郊购买了一套二手住房。
就是这个从小酷爱戏曲艺术的陈峥,世民对他特别看好,鼓励他“勇敢逐梦,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告诫他“人的一辈子不可能干得了很多件事情。你要专心致志地把一件事做好!”高中毕业,陈峥考取了中国戏剧学院戏曲导演专业。其后,又考入俄罗斯国立舞台学院攻读硕士。
从表面上看,世民性格狷狂直硬,不好相与。可是,一涉及学生,他却似乎变了一个人,异常温和细致,有时甚至有些婆婆妈妈的:“杨明星昨天考贵池区融媒体中心,不知道考得怎样?”“万余胜三十岁了,还没对象。老江,你能不能帮他介绍介绍?”当得知陈峥留学归来,暂时没有找到合适工作时,他“哀求”陈峥:“你发狠读书啊,读博士入高校吧!”
耕耘就有收获,付出必有回报。他的学生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万余胜注册了“秋浦小万”视频号,挖掘传播池州历史文化知识。目前,这个自媒体账号被业内公认为“池州最具专业水平”视频号之一;杨明星成长为贵池区融媒体中心视频部主任,妥妥的业务骨干,挑起了地方视频文化宣传的大梁;陈峥潜心戏曲艺术保护传承,牵头成功恢复失传80多年的剡溪目连戏,被授予省级非遗项目石台目连戏县级代表性传承人… …
世民当过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还在社会机构上过课,他一生中究竟培养出多少个万余胜、杨明星、陈峥?
在教育园地操碎了心,在池州地域文化研究领域拓荒不停,在学术“田地”里细作深耕……连续多年的超负荷“耕耘”透支了世民的身体,耗尽了他的心力,迫使他停止了“耕作”的步伐。2024年2月3日,世民这支原本燃烧得特别旺盛的“火把”熄灭了——他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
世民患病期间,我和他的朋友、学生们曾不止一次劝说他到大城市去寻找更好的医疗条件,他坚拒不去。当时,我们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抢抓时间撰写他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就包括这本《南山耕余录》。唉,他这是以身为薪,薪尽火传啊!
书房中眯着眼阅读古籍、图书馆内一页页一行行地查找资料、村野里细致入微地考察文化遗迹 ……转眼,世民离世一年多了,但至今他生前学习和工作的一幅幅画面仍时常浮现于我的眼前。恍惚中,这些画面又与一组历史影像叠化在一起:双目失明的左丘明摸索着刻写《国语》、伏生全家不要命地守护《尚书》、顾炎武大声呐喊“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马衡等学者冒着日寇的炮火护卫着故宫文物南迁、叶嘉莹用一生光阴传递中华诗词文化……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深刻理解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真正明白了我们中华文明为什么会几千年绵延不绝、弦歌不辍。
“路漫漫其修远兮!”文化传承的道路上,世民等先行者燃起的火势正旺。火光映路,我辈当奋力前行!
谨以此文悼念挚友世民,并为其遗著《南山耕余录》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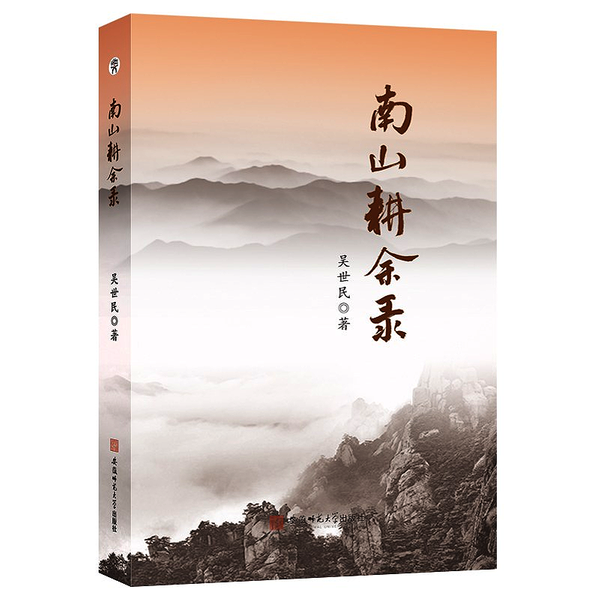
《南山耕余录》
我与世民相交时间不算太长,只有十余年,但交着交着,渐成挚友。在我的印象里,他始终是忙忙碌碌的。世民常称自己是“耕夫”,我感觉这个自称挺“对”他的。他似乎每天都在“挖栽种浇收”,“唧唧复唧唧”,没有一刻消停过。刚开始,我十分疑惑:你一个大学老师,没有学生升学的压力,怎么会这么忙?交往久了,终于理解了:他确实忙,比我想象的还要忙。因为,有那么多“田地”需要他去“耕耘”。而且,以他喜欢较真碰硬的做事风格,花费时间和精力之多可想而知。同时,我也由衷地认为,他的“忙”,忙得确有价值,有很大价值!
一、深耕学术“田地”,钻研既深且广
世民最喜欢一个词——厚积薄发。他认为,作为一个学者首先要有深厚的“内功”,必须具备丰厚的学术积淀,要“致广大而尽精微”——一方面,要使自己具备宏观视野和广泛覆盖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掌握既“微”且“精”的知识。怎样达到这种境界?“读书,多读书!”世民曾回忆自己的学生生涯说“每上一所新的学校,图书馆里,除了英语之类的书,差不多都被我扫荡一空”。参加工作后,他读书依旧“ 贪婪成性”。与专业相关联的书,他广泛读,深入读;与专业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的书,只要发现有价值或者感兴趣,他必设法罗致,饭不吃也要把它看完。海量读书,虽然占用了他的不少生命空间,但也极大地培厚了他的学养,增强了他的学力。自然,做起学问来也就裕如了。
打开2022年出版的他的学术专著《碰撞·融合·创生——吴越楚文化交融视野下的池州历史变迁》,你就会发现,这本35万字的专著内容极其闳富,系统阐述了从商代中晚期一直到当代池州地域文明的发展演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技、地理、宗教、考古、农业、建筑、冶炼、造纸诸多领域,有许多发现和创见,比如,“宣纸本为池纸。”他认为,“称为宣纸的原因是,该纸的产地是池州地域内的秋浦县。秋浦县在唐代的前期属宣州管辖。此段时间内,泾县以及宣州其他各县均未产纸(《新唐书》《元和郡县志》记载)。乃至宋时,宣州其他各县仍不产纸(《宋史》)。故至北宋时,宣纸一词已成为池纸固定的专指。”这一发现,还原了中国造纸文明一段真实状况。还有,他对池州市和黄山市境内古“ 南江”遗址路线的发现及论证,修正了《水经注》研究权威陈桥驿教授“古南江不存在”的论断,是当代《水经注》学研究的一个新突破。
这本《南山耕余录》虽然在世民笔下仅仅是“耕余之录”,但是依旧充满着学术色彩。其中,上篇第三章到第五章,学术色彩最浓。在第三章《南山悟道录》里,他从社会原因、理论溯源、“《四书》学”内涵等方面解析了《四书》与“三教归一”的因缘关系,很有思想启发性;他辩证比对了老子的“圣人”学说和庄子的“真人”学说,指出“‘真人学说’是对‘圣人学说’的补充、深化和发展”,拓展了现代学者钱穆关于老子、庄子学说歧异的理论。在第四章《南山寻古录》,他考证了长江文化与青弋江文化的地理衔接、陵阳山与道教文化、南太原郡在池州的迁转、唐代大诗人李白流寓秋浦的文化之旅、杜牧与《清明》诗的创作、画坛巨匠黄宾虹旅居池阳的绘画创作、宋朝大书法家沈辽隐居齐山的诗歌创作等。第五章《南山谈艺录》则就诗歌创作、绘画艺术、书法技法、文体兴盛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有些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比如“书拘于形划,画拘于形色者,匠也;唯书以写心,画以达意者,可以为师”“定画品先察修养”“鹧鸪意象自李白始大”“诗有画境、情境、意境”等。
即使在偏于记录和感悟生活的上篇第一章《南山樵采录》、第二章《南山闲居录》和分类汇集个人诗词歌赋的下篇第六到第十一章,也不乏学术气息。在《南山樵采录》中,他探析了池州的茶文化、造纸技术、动植物资源等;在《南山闲居录》中,他又对传统节俗、饮食、生死文化等展开论述。他的诗词歌赋大量用典,尽显学者之风。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其《池州赋》《杏花村赋》与四十余首咏史诗。这些诗赋非有厚实的史学功底不能为。
为什么一本随笔性质的文集有如此浓郁的学术色彩?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求真知、觅真理已经成为他的生命品质。”
二、执着池州地域文化研究与保护,开辟荆榛成“良田”
池州建市时间短,地域文化研究基础薄弱,系统研究接近荒芜。世民阅历丰富,视野宽阔,涉猎广泛,原本可以选择一些“时尚”的专业作为主攻方向。这样,可以“多快好省,易出成果”。可他却不顾劝阻,毅然决然地凝心于池州地域文化研究。我曾问过世民:“你研究生读的是科技哲学史专业,为什么现在却搞起了池州地域文化研究来?这可是个冷门,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经验可借鉴,难出成果啊!”世民回答道:“但尽人事,莫问前程!”顿了会,他又说:“我搞研究,不是为了凑热闹,是看社会和地方是否有需要,是否有价值。”说着说着,他的眼里泛起光:“池州是一个既年轻又古老的城市。在这片土地上,距今约30万年就出现了华龙洞人,这有可能是东亚地区向智人演化的最早古人类。商代中晚期,这里便有了青铜文明和稻作文化。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有了建城历史。作为池州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么灿烂的地域文化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研究地域文化,首先需要有文献做底。新中国成立以来,池州历经多次撤建,文献档案流落各地,找寻异常困难。为了找到所需文献,他四处奔走。既到过北京、上海、合肥、安庆等处图书馆、档案馆,也走街串巷、进村入户翻找资料。史书、方志、家谱、文集、回忆录… …一本本地翻阅,一遍遍地“耙梳”,看过的书籍资料难以计数。世民视力不好,看书喜欢眯着眼。至今,我的眼前还时不时闪现一幅画面:月儿高挂天空,与池州城西郊某小区顶楼一个窗户透出的光遥相呼应。世民置身窗前故纸堆中,手拿一本线装书,凑着台灯,眯缝着眼分辨着… …
世民尤其注重田野调查。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格物致知”,田野调查曾经是古人治学的“刚需”:孔子周游列国而后删述“六经”,司马迁为著《史记》“行万里路”,郦道元踏遍千山万水成就《水经注》,梁思成、林徽因冒着战火辗转全国各地考察研究古建筑……但是,毋庸讳言,近年来,浮躁之风蔓延至学术研究领域。在文史界,能潜心耙梳古籍的人都不多,一些研究者甚至要靠“百度”过活,更不要说去做“费钱费力费时间”的田野调查了。有人曾委婉地提醒世民,“你这学问做得太累了,效率太低了。”世民笑了笑,依然故我。
他曾四十多次前往古石城县、秋浦县遗址所在地考察,厘清了古石城县、秋浦县文化发展脉络。为了寻找春谷古县城遗址,他冒着高温酷暑跑了一次又一次。有时,头天去看了,晚上躺在床上有了疑问,第二天立马又去现场。为了寻找古南江故道,他结合郦道元《水经注》和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的记载,跋山涉水仔细勘察,并请人用无人机航拍进行辨析,终于弄清了古南江的大致流程、流域。他的田野考察经历,这本《南山耕余录》上篇第二章《南山闲居录》、第四章《南山寻古录》和下篇诗词诸章有所记载和反映,但这仅仅只是他诸多田野考察的一小部分。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两件事就没有记录。
第一件事在2023年7月。记得一天世民告诉我,说他考察了多次,认为唐朝大诗人李白的《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一诗的创作大概率与青阳县陵阳镇境内琉璃岭有关。我很兴奋,说,“这个发现很好。我抽时间来拍一个与之有关的电视短片。”8月份,我发现他病情加重,走路都有些摇摇晃晃,就说,“你身体已经这样了,暂时不去。等你身体恢复了我们再去。”9月底的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兴奋地说:“可以基本确定了!李白的《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一诗写到琉璃岭。这诗的第一句是‘霜凋楚关木’。我刚又去了琉璃岭,了解到这里过去有个寺庙就叫‘郢关寺’。综合其他因素,可以确定我之前的推断是正确的。”我顿时无语——世民,你病情很重,你正在进行血液透析治疗啊!
第二件事发生在世民去世前的一个月。当时,我正带着团队拍摄寻古秋浦县系列电视专题。他知道了,要陪我们一起去。我以他需要定期透析治疗为由没有答应。他反复说他不是天天透析,透析间隙可以去。不去,心里憋得难受,更不利于治疗。我知道他的个性,拗不过他,只能让他前往。那一次,找到了《光绪贵池县志》记载的陶渊明衣冠冢遗址,他高兴得像个孩子。
这些年,世民究竟跑了多少路?考察了多少地方?考察什么?这些现在已经无法寻找答案了,我的脑子里只浮现出一句诗词“八千里路云和月”。
功不唐捐。这种独特的“吴氏研究法”虽然在某些“聪明人”看来“很笨”,但正是依靠这种“很笨”的研究方法和十多年如一日寂寞中的坚守,世民硬是在池州地域文化研究领域开拓出一片又一片“良田”:他初步还原了吴、越、楚文化碰撞、融合,从而创生出池州地域文明的过程与内容;他系统地梳理出池州府治及辖县县治的历史变迁,深度发掘了杏花村文化、古石城— — 秋浦文化与九华山、齐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他考证出李白现存关于池州诗歌创作的全部篇目,并系统阐释了这55首诗歌涉及的具体地点、创作背景、内容、精神内核与意象特点。这些,从《南山耕余录》中可以管窥之。
世民潜心研学、淡泊名利,直至离世,职称还只是个“副教授”。但他的学术能力却得到了业界广泛认可,被聘为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会员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特聘研究员。
我想,这些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学术成绩的充分肯定,更意味着池州地域文化研究得到了省里、国家乃至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三、乐种“公田”,精耕“自留地”
世民在世之日,我曾笑他有两个特别之“好”。
一是“好管闲事”。
记得去年九月的一天,他跑到我单位,找到我说:“ 青阳县杨田镇境内有好几座古老的石拱桥,非常漂亮。老江,你是记者,去拍拍,呼吁要加强保护。”我说我们去报道要申报。过了两天,他就打来电话“申报通过了没?要尽快报道,引起方方面面的重视。”那段时间,由于其他方面工作较多,我们没有时间去采访。他就隔三差五地打电话催促。我哭笑不得,回他说“你急什么?你哪是文管所的?好管闲事了啊!”他说:“这怎么是闲事呢?这是公众的事,人人有责。我发现了就要管。”不久,我们摄制了专题片《十里东堡悠悠古桥》。
这本《南山耕余录》还收录一份市政协提案——《关于建立昭明文化遗址公园的建议》。世民不是政协委员,这份提案怎么会出现在他的文集里呢?原来,他发现始建于唐朝的梁昭明太子庙遗址尚存,但没有得到恢复和开发,便邀请一名文艺界市政协委员实地考察,并一同撰写了这份建议,由该委员提交上去。这份提案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目前,梁昭明太子庙遗址保护已被列入相关保护规划。
有些单位举办职工文化培训,邀请世民作历史文化讲座。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去,不管有钱没钱。他说,这是机会,可以传播池州历史文化。《池州市志》编辑工作启动,他主动要求加入,说“只要让我为修志出把力,可以不要工资,不挂名”。有些同行治学不严谨,不做认真考证,“百度”上“荡”点资料拼凑成文就发表,他“视同寇仇”。李白笔下的“水车岭”遗址被破坏,他痛斥相关负责人……有关他“好管闲事”的事例不胜枚举。有人说:“你一个学者,安静做你的学问就行了。管那么宽干吗?”他回答道:“做学问的初心是什么?经世致用!如果因为要做学问,就两耳不闻窗外事。那样的学问不做也罢。”
二是“好为人师”。
世民在自己所在的池州开放大学(原池州电大),先后担任学校办公室、教学处和教研室副主任,教学、管理与科研任务相当重,加上他做事较真,又“好管闲事”,本来就够忙碌的。有几年,还去池州学院兼职教学。当时他职称不高,课时费很低。显然,兼职不是为了钱。我见他太忙了,怕他身体吃不消,就劝他:“你忙得过来吗?你当老师没当够吗?”他憨憨一笑:“当老师永远当不够。”然后解释说,这些大学生就是文化传播的火种。激活他们对文化传承的热情,那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世民在池州学院兼职教学,有两个学生对池州地域文化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一个叫万余胜,另一个叫杨明星,都来自皖北阜阳市。世民就经常给他们“开小灶”。比如,利用节假日带领他们到池州各地考察历史文化,激发他们多读书。
在世民的影响下,万余胜和杨明星大学毕业后都留在了池州,都对历史文化研究感兴趣。其中,万余胜在一家艺培机构执教,他喜欢把学生带到老师吴世民家接受文化熏染。自然,这些人又成了世民的学生。不过,把学生招到家中,世民可是要“赔本”的。万余胜曾经回忆过那段经历:“毕业后我陆续带了好几个‘徒子徒孙’到吴老师家里。每个人吴老师都热情欢迎,小课堂一开就是三四个小时。不收费。”“他靠记忆普及池州历史文化,如数家珍,精确到年月日。”一个叫陈峥的学生对一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吃饭吴老师从不让我们结账,都是他自掏腰包。一般人往往是说说而已,最多推三次就结束了这个回合。而他每次都真付钱。他说我们学生没有钱。”陈峥他们并不知道,当时,他们敬爱的吴老师其实也没什么钱。依靠住房公积金和亲戚朋友的借款,他才好不容易在房价远低于城中的城郊购买了一套二手住房。
就是这个从小酷爱戏曲艺术的陈峥,世民对他特别看好,鼓励他“勇敢逐梦,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告诫他“人的一辈子不可能干得了很多件事情。你要专心致志地把一件事做好!”高中毕业,陈峥考取了中国戏剧学院戏曲导演专业。其后,又考入俄罗斯国立舞台学院攻读硕士。
从表面上看,世民性格狷狂直硬,不好相与。可是,一涉及学生,他却似乎变了一个人,异常温和细致,有时甚至有些婆婆妈妈的:“杨明星昨天考贵池区融媒体中心,不知道考得怎样?”“万余胜三十岁了,还没对象。老江,你能不能帮他介绍介绍?”当得知陈峥留学归来,暂时没有找到合适工作时,他“哀求”陈峥:“你发狠读书啊,读博士入高校吧!”
耕耘就有收获,付出必有回报。他的学生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万余胜注册了“秋浦小万”视频号,挖掘传播池州历史文化知识。目前,这个自媒体账号被业内公认为“池州最具专业水平”视频号之一;杨明星成长为贵池区融媒体中心视频部主任,妥妥的业务骨干,挑起了地方视频文化宣传的大梁;陈峥潜心戏曲艺术保护传承,牵头成功恢复失传80多年的剡溪目连戏,被授予省级非遗项目石台目连戏县级代表性传承人… …
世民当过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还在社会机构上过课,他一生中究竟培养出多少个万余胜、杨明星、陈峥?
在教育园地操碎了心,在池州地域文化研究领域拓荒不停,在学术“田地”里细作深耕……连续多年的超负荷“耕耘”透支了世民的身体,耗尽了他的心力,迫使他停止了“耕作”的步伐。2024年2月3日,世民这支原本燃烧得特别旺盛的“火把”熄灭了——他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
世民患病期间,我和他的朋友、学生们曾不止一次劝说他到大城市去寻找更好的医疗条件,他坚拒不去。当时,我们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抢抓时间撰写他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就包括这本《南山耕余录》。唉,他这是以身为薪,薪尽火传啊!
书房中眯着眼阅读古籍、图书馆内一页页一行行地查找资料、村野里细致入微地考察文化遗迹 ……转眼,世民离世一年多了,但至今他生前学习和工作的一幅幅画面仍时常浮现于我的眼前。恍惚中,这些画面又与一组历史影像叠化在一起:双目失明的左丘明摸索着刻写《国语》、伏生全家不要命地守护《尚书》、顾炎武大声呐喊“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马衡等学者冒着日寇的炮火护卫着故宫文物南迁、叶嘉莹用一生光阴传递中华诗词文化……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深刻理解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真正明白了我们中华文明为什么会几千年绵延不绝、弦歌不辍。
“路漫漫其修远兮!”文化传承的道路上,世民等先行者燃起的火势正旺。火光映路,我辈当奋力前行!
谨以此文悼念挚友世民,并为其遗著《南山耕余录》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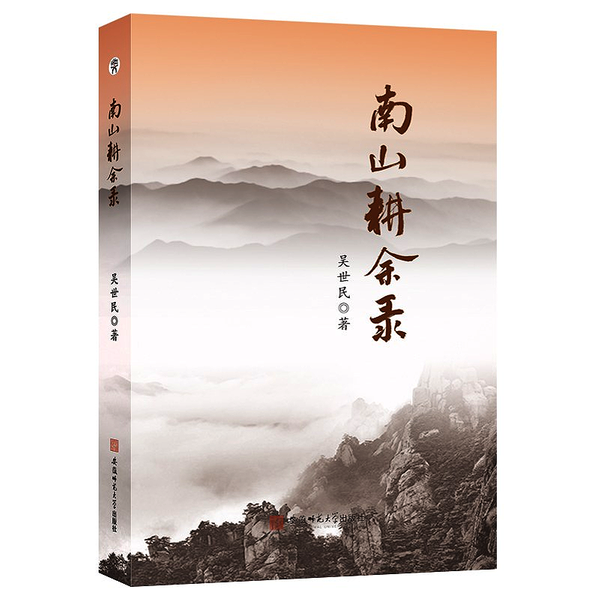
《南山耕余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