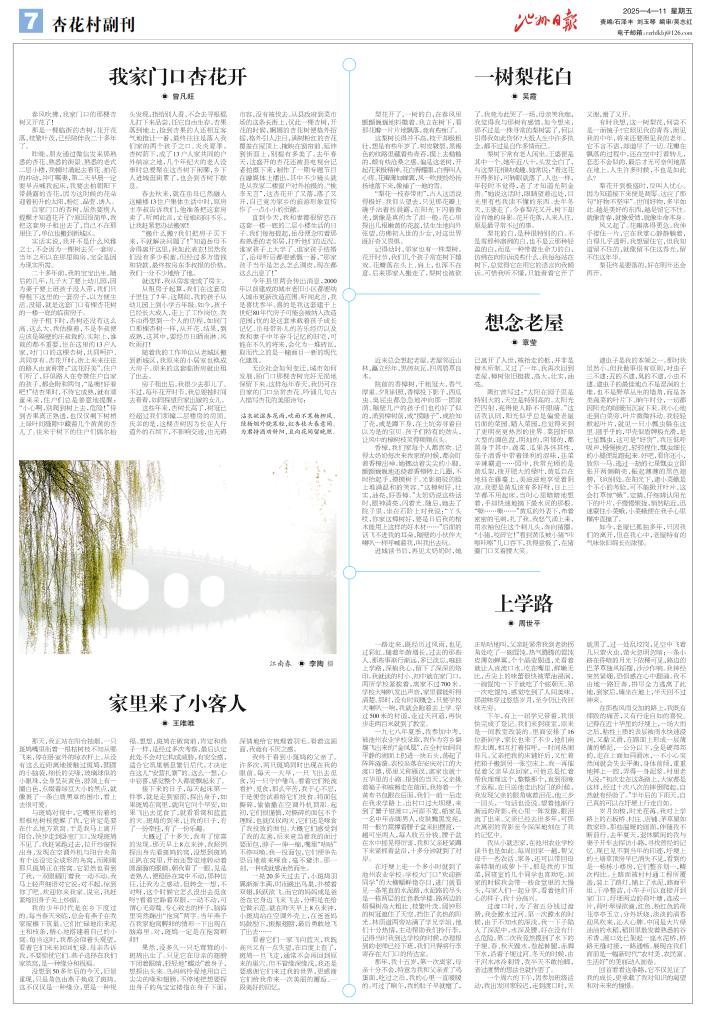发布日期:
2025年04月11日
上学路
一路走来,既经历过风雨,也见过彩虹。随着年龄增长,过去的那些人、那些事渐行渐远,多已淡忘,唯独上学路,深植我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就读的村小、初中就在家门口,两所学校紧挨着,离家不过700米。学校大喇叭发出声音,家里都能听得清楚。那时,没有时间概念,只要学校大喇叭一响,我就会跑着去上学。穿过500米的村道,走过天河道,再快步走两百米就到了教室。
一九七八年夏季,我参加中考,被池州农业学校录取,我作为穷乡僻壤飞出来的“金凤凰”,在全村如同向平静的湖面上扔进一块石头,荡起了阵阵涟漪。农校坐落在安庆对江的大渡口镇,那里又称雁汊,离家也就十五华里的小路。报到的当天,父亲挑着箱子和被褥走在前面,我挎着一个黄布书包跟在后面,我们一前一后走在我求学路上。出村口过大坝埂,来到了蟹子钳渡口,河面不宽。船家是一名中年赤脚男人,皮肤黝黑发亮,用一根竹篙撑着腰子盆来回摆渡,一趟可坐两人,每人收五分钱。腰子盆在水中摇晃得厉害,我和父亲赶紧蹲下来紧抓着盆沿,十多分钟就到了对岸。
在圩埂上走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池州农业学校。学校大门口“欢迎新同学”的大横幅鲜艳夺目,进门就看见一条笔直的水泥路,水泥路的尽头是一栋两层的红色教学楼。路两边的梧桐树高大粗壮、枝繁叶茂。阔钟形的树冠遮住了天空,挡住了炙热的阳光。林荫道两旁站满了学兄学姐,他们十分热情,主动帮助我们拎行李。记得当时我到达学校的时候,办理报到的老师已经下班,我们只得将行李寄存在大门口的传达室。
那年,我十五岁,第一次离家,母亲十分不舍,特意为我和父亲煮了鸡蛋面,吃过之后,我的心里一直暖暖的。可过了晌午,我的肚子早就瘪了,正咕咕地叫,父亲赶紧带我到老街拐角处吃了一碗馄饨。热气腾腾的馄饨皮薄如蝉翼,个个晶莹剔透,光看着就让人直流口水。吃在嘴里,鲜嫩无比,舌尖上的味蕾很快被荤油浸润,一碗馄饨一下子就吃了个底朝天。第一次吃馄饨,感觉吃到了人间美味,那滋味穿过悠悠岁月,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下午,有上一届学兄带着,我很快完成了登记。我们来到寝室,原来是一间教室改装的。里面安排了16位新同学,家长也来了不少,他们南腔北调,相互打着招呼,一时间热闹非凡。父亲把我的床铺好后,又忙着把箱子搬到另一张空床上。我一再催促着父亲早点回家,可他总是忙着帮我理理这个,整整那个,直到很晚才返程。在目送他走出校门的时候,我发现父亲的眼角噙着泪花,他三步一回头,一句话也没说。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心里一阵发酸,眼泪流了出来。父亲已经去世多年,可那次离别的背影至今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我从小就恋家,在池州农业学校读书也是如此。每周回家一趟,帮父母干一些农活、家务,还可以带回母亲特制的咸萝卜干,那是我的下饭菜,同寝室的几个同学也喜欢吃。回家的时候我会带一些食堂里的大馒头,与家人们一起分享,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十分高兴。
过渡口时,为了省五分钱过渡费,我会蹚水过河。第一次蹚水的时候,由于不知水的深浅,我一下子陷入了深泥中,水深及腰,好在没有什么危险。第二次我竟然摸到了水下的子埂。春、秋天蹚水,卷起裤腿,赤脚下水,沿着子埂过河。冬天的时候,由于河水冰冷刺骨,我半天不敢抬脚,省过渡费的想法也就作罢了。
一个周六的下午,因参加班级活动,我出发回家较迟,走到渡口时,天就黑了,过一处乱坟岗,见空中飞着几只萤火虫,萤火忽明忽暗;一条小路在昏暗的月光下依稀可见,路边的巴茅草随风摇摆,沙沙作响。我神经突然紧绷,恐惧感在心中翻涌。我不由地一路狂奔,拼尽全力逃离了此地,到家后,瘫坐在地上,半天回不过神来。
在那些风雨交加的路上,我既有摔跤的痛苦,又有行走自如的喜悦。记得在近十华里的圩埂上,一场大雨之后,粘性土质的表层被雨水快速浸润,又黏又滑,在路面上形成一层薄薄的稀泥,一公分以下,全是硬邦邦的,走在上面如同滑冰,一不小心突然间就会失去平衡,身体前倾,重重地摔上一跤,弄得一身泥浆。村里老人说:“初次走在这条路上,大家都是这样,经过十次八次的摔倒爬起,自然就有经验了。”半年后的下雨天,自己真的可以在圩埂上行走自如。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我对上学路上的石板桥、村庄、店铺、茅草屋如数家珍,那些温暖的画面,伴随我不断前行。去年夏天,退休赋闲的我与妻子开车去探访小路,寻找曾经的记忆。现已见不到当年的印迹,圩埂上的土墙草顶房早已消失不见,看到的是一栋栋小楼房,它们整齐划一,鳞次栉比。土路面被村村通工程所覆盖,装上了路灯,铺上了水泥,路面平坦、干净整洁,小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圩埂两边的荷叶塘,连成一片,荷叶翠绿欲滴,红色、粉红色的荷花亭亭玉立,分外妖娆,淡淡的清香迎风吹来,沁人心脾。中间是大片绿油油的水稻,稻田里散发着熟悉的谷禾香。渡口处已架起一座水泥桥,桥路无缝对接,一路通畅。展现在我们面前是一幅新时代“农村美、农民富、生活好”的美丽动人画卷。
回首看看这条路,它不仅见证了我的成长,更承载了我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
一九七八年夏季,我参加中考,被池州农业学校录取,我作为穷乡僻壤飞出来的“金凤凰”,在全村如同向平静的湖面上扔进一块石头,荡起了阵阵涟漪。农校坐落在安庆对江的大渡口镇,那里又称雁汊,离家也就十五华里的小路。报到的当天,父亲挑着箱子和被褥走在前面,我挎着一个黄布书包跟在后面,我们一前一后走在我求学路上。出村口过大坝埂,来到了蟹子钳渡口,河面不宽。船家是一名中年赤脚男人,皮肤黝黑发亮,用一根竹篙撑着腰子盆来回摆渡,一趟可坐两人,每人收五分钱。腰子盆在水中摇晃得厉害,我和父亲赶紧蹲下来紧抓着盆沿,十多分钟就到了对岸。
在圩埂上走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池州农业学校。学校大门口“欢迎新同学”的大横幅鲜艳夺目,进门就看见一条笔直的水泥路,水泥路的尽头是一栋两层的红色教学楼。路两边的梧桐树高大粗壮、枝繁叶茂。阔钟形的树冠遮住了天空,挡住了炙热的阳光。林荫道两旁站满了学兄学姐,他们十分热情,主动帮助我们拎行李。记得当时我到达学校的时候,办理报到的老师已经下班,我们只得将行李寄存在大门口的传达室。
那年,我十五岁,第一次离家,母亲十分不舍,特意为我和父亲煮了鸡蛋面,吃过之后,我的心里一直暖暖的。可过了晌午,我的肚子早就瘪了,正咕咕地叫,父亲赶紧带我到老街拐角处吃了一碗馄饨。热气腾腾的馄饨皮薄如蝉翼,个个晶莹剔透,光看着就让人直流口水。吃在嘴里,鲜嫩无比,舌尖上的味蕾很快被荤油浸润,一碗馄饨一下子就吃了个底朝天。第一次吃馄饨,感觉吃到了人间美味,那滋味穿过悠悠岁月,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下午,有上一届学兄带着,我很快完成了登记。我们来到寝室,原来是一间教室改装的。里面安排了16位新同学,家长也来了不少,他们南腔北调,相互打着招呼,一时间热闹非凡。父亲把我的床铺好后,又忙着把箱子搬到另一张空床上。我一再催促着父亲早点回家,可他总是忙着帮我理理这个,整整那个,直到很晚才返程。在目送他走出校门的时候,我发现父亲的眼角噙着泪花,他三步一回头,一句话也没说。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心里一阵发酸,眼泪流了出来。父亲已经去世多年,可那次离别的背影至今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我从小就恋家,在池州农业学校读书也是如此。每周回家一趟,帮父母干一些农活、家务,还可以带回母亲特制的咸萝卜干,那是我的下饭菜,同寝室的几个同学也喜欢吃。回家的时候我会带一些食堂里的大馒头,与家人们一起分享,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十分高兴。
过渡口时,为了省五分钱过渡费,我会蹚水过河。第一次蹚水的时候,由于不知水的深浅,我一下子陷入了深泥中,水深及腰,好在没有什么危险。第二次我竟然摸到了水下的子埂。春、秋天蹚水,卷起裤腿,赤脚下水,沿着子埂过河。冬天的时候,由于河水冰冷刺骨,我半天不敢抬脚,省过渡费的想法也就作罢了。
一个周六的下午,因参加班级活动,我出发回家较迟,走到渡口时,天就黑了,过一处乱坟岗,见空中飞着几只萤火虫,萤火忽明忽暗;一条小路在昏暗的月光下依稀可见,路边的巴茅草随风摇摆,沙沙作响。我神经突然紧绷,恐惧感在心中翻涌。我不由地一路狂奔,拼尽全力逃离了此地,到家后,瘫坐在地上,半天回不过神来。
在那些风雨交加的路上,我既有摔跤的痛苦,又有行走自如的喜悦。记得在近十华里的圩埂上,一场大雨之后,粘性土质的表层被雨水快速浸润,又黏又滑,在路面上形成一层薄薄的稀泥,一公分以下,全是硬邦邦的,走在上面如同滑冰,一不小心突然间就会失去平衡,身体前倾,重重地摔上一跤,弄得一身泥浆。村里老人说:“初次走在这条路上,大家都是这样,经过十次八次的摔倒爬起,自然就有经验了。”半年后的下雨天,自己真的可以在圩埂上行走自如。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我对上学路上的石板桥、村庄、店铺、茅草屋如数家珍,那些温暖的画面,伴随我不断前行。去年夏天,退休赋闲的我与妻子开车去探访小路,寻找曾经的记忆。现已见不到当年的印迹,圩埂上的土墙草顶房早已消失不见,看到的是一栋栋小楼房,它们整齐划一,鳞次栉比。土路面被村村通工程所覆盖,装上了路灯,铺上了水泥,路面平坦、干净整洁,小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圩埂两边的荷叶塘,连成一片,荷叶翠绿欲滴,红色、粉红色的荷花亭亭玉立,分外妖娆,淡淡的清香迎风吹来,沁人心脾。中间是大片绿油油的水稻,稻田里散发着熟悉的谷禾香。渡口处已架起一座水泥桥,桥路无缝对接,一路通畅。展现在我们面前是一幅新时代“农村美、农民富、生活好”的美丽动人画卷。
回首看看这条路,它不仅见证了我的成长,更承载了我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