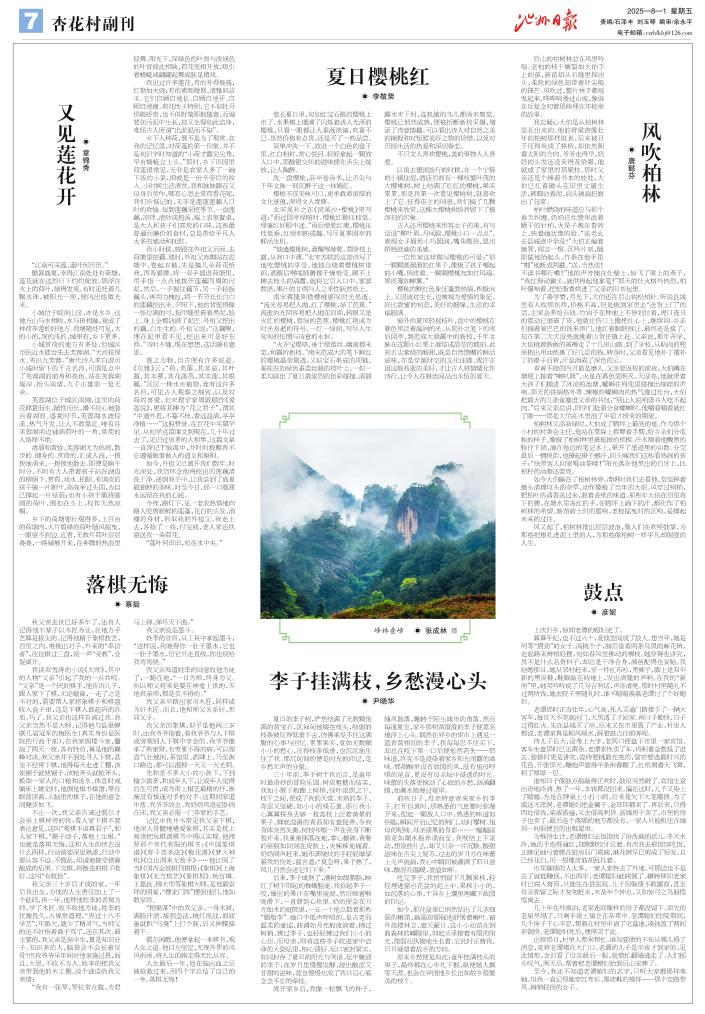发布日期:
2025年08月01日
落棋无悔
我父亲去世已好多年了,还有人记得他半辈子以木匠为业,在地方手艺算是拔尖的。记得他精于象棋技艺,百里之内,难挑出对手,外来的“串访者”,往往棋过三盘,说一声“受教”,仓促离开。
我读双雪涛的小说《大师》,其中的人物“父亲”引起了我的一点共鸣。“父亲”是一个民间棋手,他告诉儿子,跟人家下了棋,无论输赢,一走了之是不对的,需要帮人家将象棋子和棋盘收入盒子里,这是下棋人最起码的品质。巧了,我父亲也这样告诫过我。我父亲当然不是大师,记得他与县里蝉联几届冠军的梅医生(真实身份是医院的行政干部),在我家阁楼斗室,鏖战了两天一夜,各有胜负,算是他的巅峰对决。我父亲并不到处寻人下棋,甚至不经常下棋,他得每天走进工棚,该使锯子就使锯子,该轮斧头就轮斧头,换取一家人的口粮和汤水。休息时或躺床上睡觉时,他倒是棋书棋谱,擎在眼前读着,头脑里的棋子,在他的意念间健步如飞。
不止一次,我父亲告诫过偶尔才会坐上棋枰旁的我:看人家下棋不要表达意见,这叫“观棋不语真君子”,和人家下棋,“摸子动子,落地土生根。”也就是落棋无悔,这和人生的状态没什么两样,行动前要深思熟虑,行动中要从容不迫、不慌乱,坦诚地接受错算酿成的后果。下完棋,将散迭的棋子收好,这叫“有收捡”。
我父亲三十岁后才成的家,一年后我出生,为他的人生责任加上了一个砝码,再一年,他拜他姓李的表舅为师,学了木匠。收不收他为徒,姓李的犹豫良久,古规常道理,“男过十八不学艺”,年龄大,就少了精灵气,当师父的还不好指着鼻子骂了,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我父亲是高中生,算是知识分子。知识多的人,脑袋会不会长着反骨?但我爷爷早年间对他家施过恩,而且,大恩,不收不为人。姓李的把我父亲带到他的木工棚,说个谜语给我父亲猜:
“我有一张琴,琴弦常在腹,为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
我父亲说是墨斗。
姓李的首肯,从工具中拿起墨斗,“这样说,我晓得你一肚子墨水,它也一肚子墨水,但它只走直线,你也别给我弯弯绕。”
我父亲知道姓李的同意收他为徒了,一跪在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师父将来是要在神龛上供的,天地君亲师,都是负不得的。”
我父亲半路出家当木匠,同样成为好木匠。而且,他和师父关系好,形同父子。
我父亲的象棋,似乎是他两三岁时,由我爷爷抱着,看我爷爷与人下棋或旁观别人下棋中学会的。我爷爷继承了些家财,有劳累不得的病,可以理直气壮地闲,茶馆里、酒肆上,乃至街口路边,都可以混掉一天又一天光阴。
先和差不多大小的小孩下,下到输少赢多,和成年人下,让成年人觉得后生可畏,成为街上棋艺最精的仔,渐渐没有棋逢对手的对手。这期间家道中落、我爷爷故去、我奶奶风湿症卧病在床,我父亲必需一门养家的手艺。
记忆中我并不常见我父亲下棋,他深入骨髓地嗜爱象棋,其实是枕上阅读把玩棋谱棋书中得以实现。他搜罗那个年代有限的棋书:《中国象棋谱》《弃子攻杀法》《梅花谱》《梦入神机》《自出洞来无敌手》……他订阅了当时国内全部棋刊棋报:《象棋》《上海象棋》《北方棋艺》《象棋报》。杨官璘、王嘉良、柳大华等象棋大师,是他最崇拜的明星,“摆龙门阵”摆到他们,他如数家珍。
“稻粱谋”中的我父亲,一身木屑,满脸汗渍,接到急活,挑灯夜战,很疲惫就趴“马凳”上打个盹,后又抻腰接着干。
偶尔闲暇,他便拿起一本棋书,观人生之道。他目光坚定,无视外界的风风雨雨,将人生的路走得无比从容。
人生最后一年,他在脑出血之后被抢救过来,用四个字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落棋无悔!
我读双雪涛的小说《大师》,其中的人物“父亲”引起了我的一点共鸣。“父亲”是一个民间棋手,他告诉儿子,跟人家下了棋,无论输赢,一走了之是不对的,需要帮人家将象棋子和棋盘收入盒子里,这是下棋人最起码的品质。巧了,我父亲也这样告诫过我。我父亲当然不是大师,记得他与县里蝉联几届冠军的梅医生(真实身份是医院的行政干部),在我家阁楼斗室,鏖战了两天一夜,各有胜负,算是他的巅峰对决。我父亲并不到处寻人下棋,甚至不经常下棋,他得每天走进工棚,该使锯子就使锯子,该轮斧头就轮斧头,换取一家人的口粮和汤水。休息时或躺床上睡觉时,他倒是棋书棋谱,擎在眼前读着,头脑里的棋子,在他的意念间健步如飞。
不止一次,我父亲告诫过偶尔才会坐上棋枰旁的我:看人家下棋不要表达意见,这叫“观棋不语真君子”,和人家下棋,“摸子动子,落地土生根。”也就是落棋无悔,这和人生的状态没什么两样,行动前要深思熟虑,行动中要从容不迫、不慌乱,坦诚地接受错算酿成的后果。下完棋,将散迭的棋子收好,这叫“有收捡”。
我父亲三十岁后才成的家,一年后我出生,为他的人生责任加上了一个砝码,再一年,他拜他姓李的表舅为师,学了木匠。收不收他为徒,姓李的犹豫良久,古规常道理,“男过十八不学艺”,年龄大,就少了精灵气,当师父的还不好指着鼻子骂了,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我父亲是高中生,算是知识分子。知识多的人,脑袋会不会长着反骨?但我爷爷早年间对他家施过恩,而且,大恩,不收不为人。姓李的把我父亲带到他的木工棚,说个谜语给我父亲猜:
“我有一张琴,琴弦常在腹,为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
我父亲说是墨斗。
姓李的首肯,从工具中拿起墨斗,“这样说,我晓得你一肚子墨水,它也一肚子墨水,但它只走直线,你也别给我弯弯绕。”
我父亲知道姓李的同意收他为徒了,一跪在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师父将来是要在神龛上供的,天地君亲师,都是负不得的。”
我父亲半路出家当木匠,同样成为好木匠。而且,他和师父关系好,形同父子。
我父亲的象棋,似乎是他两三岁时,由我爷爷抱着,看我爷爷与人下棋或旁观别人下棋中学会的。我爷爷继承了些家财,有劳累不得的病,可以理直气壮地闲,茶馆里、酒肆上,乃至街口路边,都可以混掉一天又一天光阴。
先和差不多大小的小孩下,下到输少赢多,和成年人下,让成年人觉得后生可畏,成为街上棋艺最精的仔,渐渐没有棋逢对手的对手。这期间家道中落、我爷爷故去、我奶奶风湿症卧病在床,我父亲必需一门养家的手艺。
记忆中我并不常见我父亲下棋,他深入骨髓地嗜爱象棋,其实是枕上阅读把玩棋谱棋书中得以实现。他搜罗那个年代有限的棋书:《中国象棋谱》《弃子攻杀法》《梅花谱》《梦入神机》《自出洞来无敌手》……他订阅了当时国内全部棋刊棋报:《象棋》《上海象棋》《北方棋艺》《象棋报》。杨官璘、王嘉良、柳大华等象棋大师,是他最崇拜的明星,“摆龙门阵”摆到他们,他如数家珍。
“稻粱谋”中的我父亲,一身木屑,满脸汗渍,接到急活,挑灯夜战,很疲惫就趴“马凳”上打个盹,后又抻腰接着干。
偶尔闲暇,他便拿起一本棋书,观人生之道。他目光坚定,无视外界的风风雨雨,将人生的路走得无比从容。
人生最后一年,他在脑出血之后被抢救过来,用四个字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落棋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