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2025年11月11日
九华山脚下骑自行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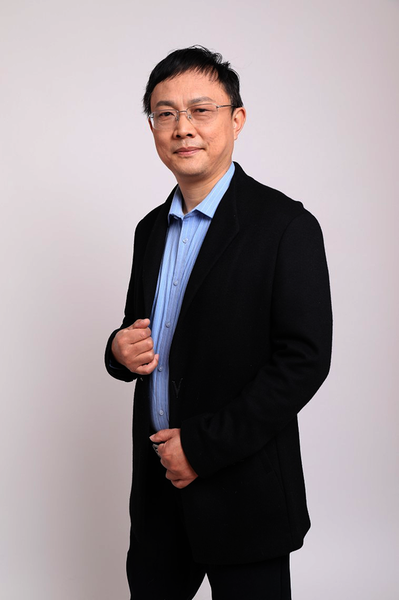
冯渊,正高级教师,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高中语文教研员,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兼任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安徽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教育出版集团语文出版社《语文建设》编委。文学作品见于《上海文学》《解放军文艺》《散文》《长城》等。著有《仰望星空从仰望伟人开始》《怎样阅读一部长篇小说》《逻辑的力量》等。
我住在山脚下的民宿里。这其实不能叫民宿,就是农民的家。他们腾出了几间房子做客房,客房里按照宾馆的标准布置。皖南山区,城市乡村都很干净。走进来,真有点“回家”的感觉,堂屋里摆着八仙桌,山墙上挂着字画。主人一家按照他们的节奏生活在这幢房子里。我订餐了,他们另外准备,杀鸡也行,油焖茄子也行,各自进餐,两不相扰。
房子离九华山风景区不远。爬山很累,下山更累,我的右腿已经不能正常行走,要一瘸一拐才能对付那无穷无尽的台阶。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就没事。这房子,能补精气神。
次日,我向房东借了一辆自行车,山不爬了,就到村子里田地溪流间转转。
有共享单车之前,自行车意味着故乡。很多年前,我随单位同事一起坐一辆面包车出游,在一个小镇停车吃饭,我借了老板的自行车在街上骑了一圈。
同事看到,惊呼:这是你的老家啊。
不是。
那你怎么会有自行车骑?
借的。
自行车的行驶半径有限,骑自行车的人,基本都在他熟悉的土地上。坐在长途客车里的人是异乡客,从长途车上下来步行,无头苍蝇一样,不辨东西。骑自行的人,悠闲,自如。我用一刻钟的骑行就熟悉了这个小镇的布局。
在九华山脚下也是这样。我在稻田田埂上骑自行车,一下子回到了故乡。
水稻正在分蘖。挺拔,青翠。土地深处有一种强劲的力量,一大片稻田在沉默中有千军万马的气息。
迎面有农人肩扛铁锹走过来,稻田里要放掉多余的水,铁锹在田埂的缺口处,缺口高低,老把式一眼就能看准,两三锹就能堆妥。铲完泥土,将锹面和锹背轮番在田埂草皮上轻轻一推一拉,擦干净,轻轻一掂,锹棍上了肩头,铁锹在他身后露出雪亮的刃口。
农人看了我一眼,附近村庄的人他都认识,眼前是个陌生人,他一时间还没想到面前是个游客,我就匆匆骑远了。
远处的青山,近处的稻田,澄鲜的空气。没有熟人的自在,有故乡田埂上的亲切。
我骑来骑去,腿一点都不酸痛了。水稻自顾自生长,人自顾自在风里飞行。
骑到一条小河边。山里流出来的水,清澈凉爽,水底的石头清晰可见。我家乡小河比这深得多,看不到水底,两岸是青蒿、苦艾、茅草、商陆。每走一步都是历险,河上行舟也得小心,水底深浅不知。这里河水易涨易退,落雨时山洪冲泻,河水向两岸弥漫;天晴久了,河里有些地方就水落石出。我在异乡找到故乡的感觉,也能分辨异乡的不同之处,这不同让我更加欣喜。
我在黑夜走过自己的村庄不会迷路,没有月亮也没有路灯时,犬吠就是向导。四旺家是一条铁包金的四眼犬,狺狺狺;听到它的叫声,走过一片竹林,经过四旺曾祖父的坟山,就到了三狗家。三狗家是一条黄柴犬,汪汪汪,敷衍了事叫三声,它听得出我的脚步。过了三狗家,就能看到我家厨房的烟囱,祖父在烟囱上面钉了一只铁马,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能听到铁马叮当作响。
九华山脚下,我一个人也不认识。稻田、河水我认识,鸡犬我都不熟悉。只有熟悉了鸡犬才能走进村庄的内部吧。
民宿让我有回家的错觉,八仙桌上一坐,我真以为回到了童年。门口鲜红的鸡冠花跟祖母种的一样。他们的口音不同,他们的微笑礼貌而陌生。我以为这恰到好处,但心里隐隐觉得不满足。于是骑车到稻田里转悠,以为这样能更熟悉九华山脚下的村庄。
村庄是有血缘关系的聚族而居,没有血亲至少也是姻亲。走在田埂上扛着大铁锹的那个中年农人,他是这里某人的父亲、表弟、女婿、姐夫、姑爷、舅舅……一朵野花也是有名字的,一根藤攀爬在一棵树上都有说法,是野豌豆花开在菜地里,是常青藤爬在水杉上。看九华山风景的异乡人,在这里没有亲戚称谓。
外乡人,要进入陌生村庄,最好的办法是入赘。但人不能常常入赘,他只能看着这些稻田上的房子,看着鸡冠花出神。房子里活动的人影都不真实,一个笑话,一桩趣事,都与他无关。他们在那里笑成一团,朝这边客房望一眼,觉得打搅了对方才压低笑声,外乡人感到一种被疏远和被隔离的苦恼。
人类总是“不安于室”,要从自己的故乡出走,要看星星怎样装饰别人的星空。深入他乡,眼神好奇,浮光掠影,要不了多久,连照片都会遗忘。
不过,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骑车在九华山脚下的稻田边,双手撒把,山风扑面而来的那一刻。
